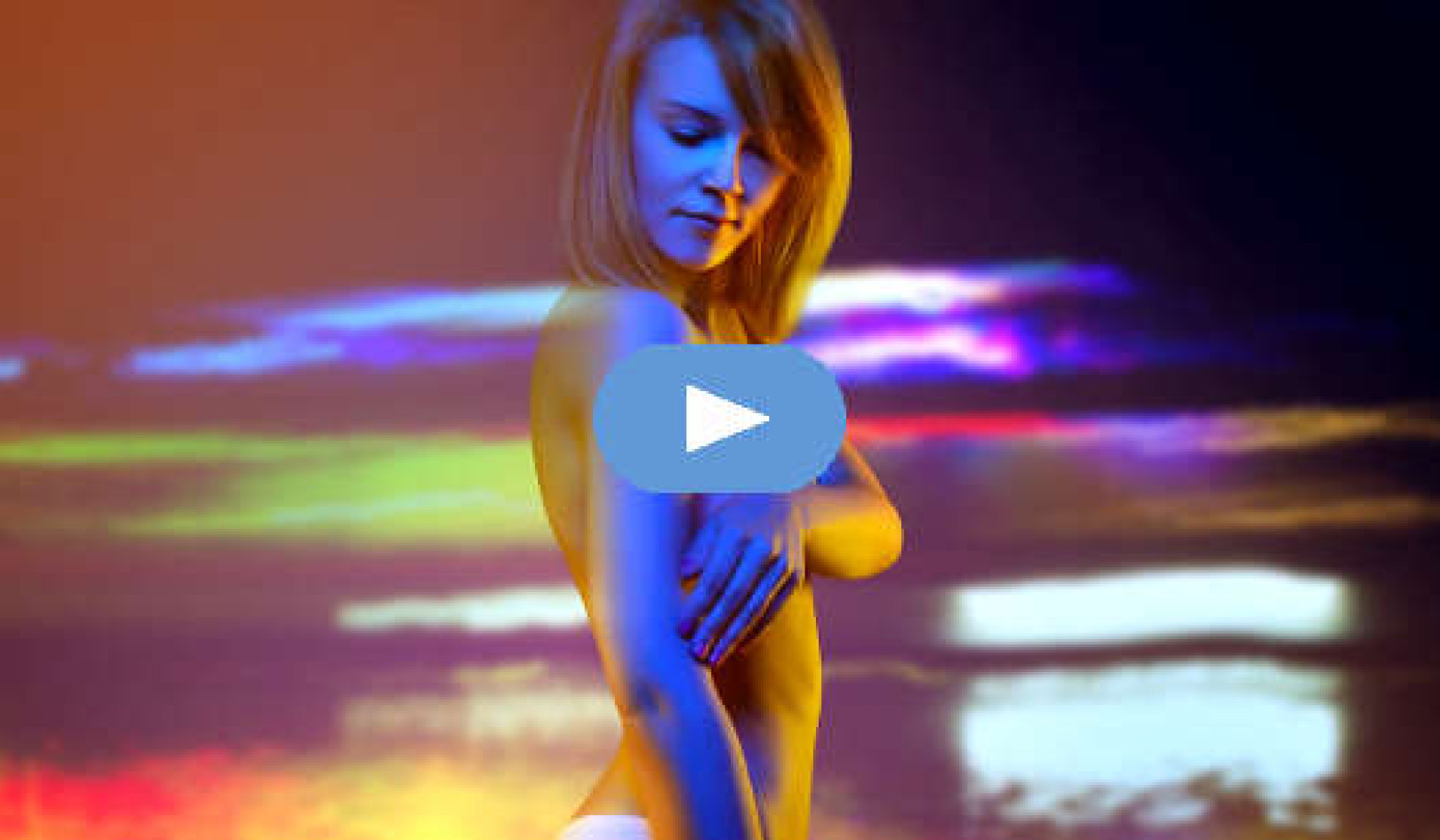美聯社照片/格里布魯姆
颶風, 龍捲風 和 野火 已經測試了我們作為個人,社區和社會的決心。 伴隨著社會危機等 政治- 和 戰爭引起的遷移這些事件清楚地說明了我們通過非正式社交網絡和正式社會機構相互適應,幫助和信任的能力。
對我們機構的信任正在下降。 雖然這種不信任可能是由於社會系統失敗或步履蹣跚的直接經歷所致, 憤世嫉俗者和權威人士可以通過投票和輿論來促進對金融和社會資本的不信任.
信任通常被編織到我們的社會中,就像一條無形的線索,將不同的個體和遙遠的社區拼接在一起。 有效的社會基於對他人的依賴和依賴,提供從移動網絡,供水和下水道服務,電力,教育和司法等各方面的服務。
為了修復它被破壞的地方,並在它破壞的地方強化它,我們必須檢查我們的社會掛毯,並詢問我們如何促進信任。
信任鄰居,領導人和機構
信任不是一種全有或全無的現象。 它可以在同齡人和領導者之間以及對機構及其像徵之間發展。
我們與同行有著共同的命運。 他們的行為對我們很重要。 當我們能夠,我們監督和調節他們的行為 通過直接觀察和行動. 當我們做不到時,我們依靠八卦和其他間接手段 了解他人及其價值觀。 如果我們認為我們沒有達到他們的標準,我們可能會加大努力。 如果我們認為我們已超出他們的期望,我們可能會減少我們的努力。
並非所有團體成員都具有同等地位。 專家和領導者在其社交網絡中佔據中心位置 - 即使只是臨時性的。 理想情況下,他們擁有可以幫助團隊的知識,能力和社會資本。
合法的專業知識很難獲得; 它 需要數年才能發展。 即使我們在一個領域有能力,專業知識也沒有彈性。 它可以縮小我們的注意力,導致我們看不到非典型模式。 這意味著領導者和專家需要在他們的專業知識中謙虛。
雖然信用可能會被聲稱 一個領導者 or 下一個 對於經濟和社會系統的運作,最終我們的社會是由合作和協作支持的幾代文化演變的最終產物。
隨著時間的推移,專家組成為我們社會的一部分。 他們成為我們信任的機構。 警察徽章,軍用徽章,法官長袍,聽診器和實驗室外套等符號 承擔新的意義,傳達和賦予這種地位。
符號變得重要
即使是複雜的科學儀器和技術也可以具有超出實際效用的象徵意義。 這些符號可用於 說服我們團隊內外的人。 它們也可以用來操縱我們的信任.
像大家一樣 專家依靠他們的同行通過正式標準和專業組織來控制他們。 科學,法律和醫學等專業都是自我反思的。 例如,Mehmet Oz博士的許多說法的揭穿,提供了這種內部規則的重要說明.
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些機制確保專業保持其信譽及其獲得財務和社會資源的機會。
信任失敗的危險
最近美國的颶風說明了對職業可信度的擔憂。 對科學的不信任在人們如何應對颶風佛羅倫薩的方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些居民出於實際原因留下來,包括保護家庭,寵物和財產。 其他人只是打折信息或 他們相信更高的力量來保護他們.
雖然這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堅定不移的個人主義,但它也可能代表著對其社區和科學機構缺乏信任。
 隨著颶風佛羅倫薩走近,許多北卡羅萊納人拒絕撤離。 是因為對當局警告的不信任? (美聯社)
隨著颶風佛羅倫薩走近,許多北卡羅萊納人拒絕撤離。 是因為對當局警告的不信任? (美聯社)
拒絕服從專家和機構的權威反映了社會凝聚力的崩潰可能對我們的生活和社區造成的實際代價。 它代表了從事實到意見和謠言的轉變。
這並不是說制度上的缺陷應該打折扣。 雖然有科學惡作劇,像 氣候科學基於共識。 在選擇信任他人時,我們必須權衡好壞。 雖然我們不能忽視不端行為, 我們絕不能 將少數人的行為誤認為多數人.
折扣信息以獲得臨時保證或社會收益 和 用虛張聲勢和自信取代它 不會讓我們成為更好的決策者。 我們生活在數據時代。 只有準確的信息和成功的應用才能改善我們的生活,並在未來保護我們。 我們需要專家和機構幫助我們使用它。
重組我們的機構
中國和羅馬的徒勞努力向我們表明,儘管它們具有像徵意義,但牆壁不會保證我們的安全。 它們是當代問題的過時解決方案。 如果我們想避免 所有人都反對霍布斯的噩夢,我們必須重新相互信任並尊重我們的機構。
我們需要透明度。 必須確定並承認重建信任的合法障礙。 結構性不平等仍然存在 與種族和性別有關。 雖然這些持續的擔憂可能是明確偏見的結果, 他們也可能反映出製度惰性。 我們必須理解這些動態,而不是試圖證明它們的合理性,以便有效地糾正這些差異。
我們的行為和我們機構的行為必須受到質疑。 問題是對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的健康和必要的回應。
最好的決定不是通過遵守我們認為是我們小組的意見而做出的。 我們必須學習 精緻的民間藝術藝術 和實踐 真實的異議.
如果我們不首先質問自己,其他人也會很樂意。
從內部來看,這可能看起來浪費而且效率低下。 從外面看,它可能會出現廣泛的異議和猶豫不決。 這是民主。
但從歷史時間線來看, 質疑我們自己的信念以及我們團隊的信念可以幫助我們做出更好的決策。 預測未來必須用幾十年和幾個世紀來完成,而不僅僅是選舉週期。 只要有可能, 我們必須從過去的類比推理,比較不同的文化 並緩沖我們對未知的必然性。
投票給領導者是不夠的。 我們必須讓我們的領導人承擔責任,無論我們是否投票支持他們或反對他們。 我們必須參與我們的社區,因為我們與他們是不可分割的。![]()
關於作者
Jordan Richard Schoenherr,心理學系兼職研究教授, 卡爾頓大學
相關書籍
at InnerSelf 市場和亞馬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