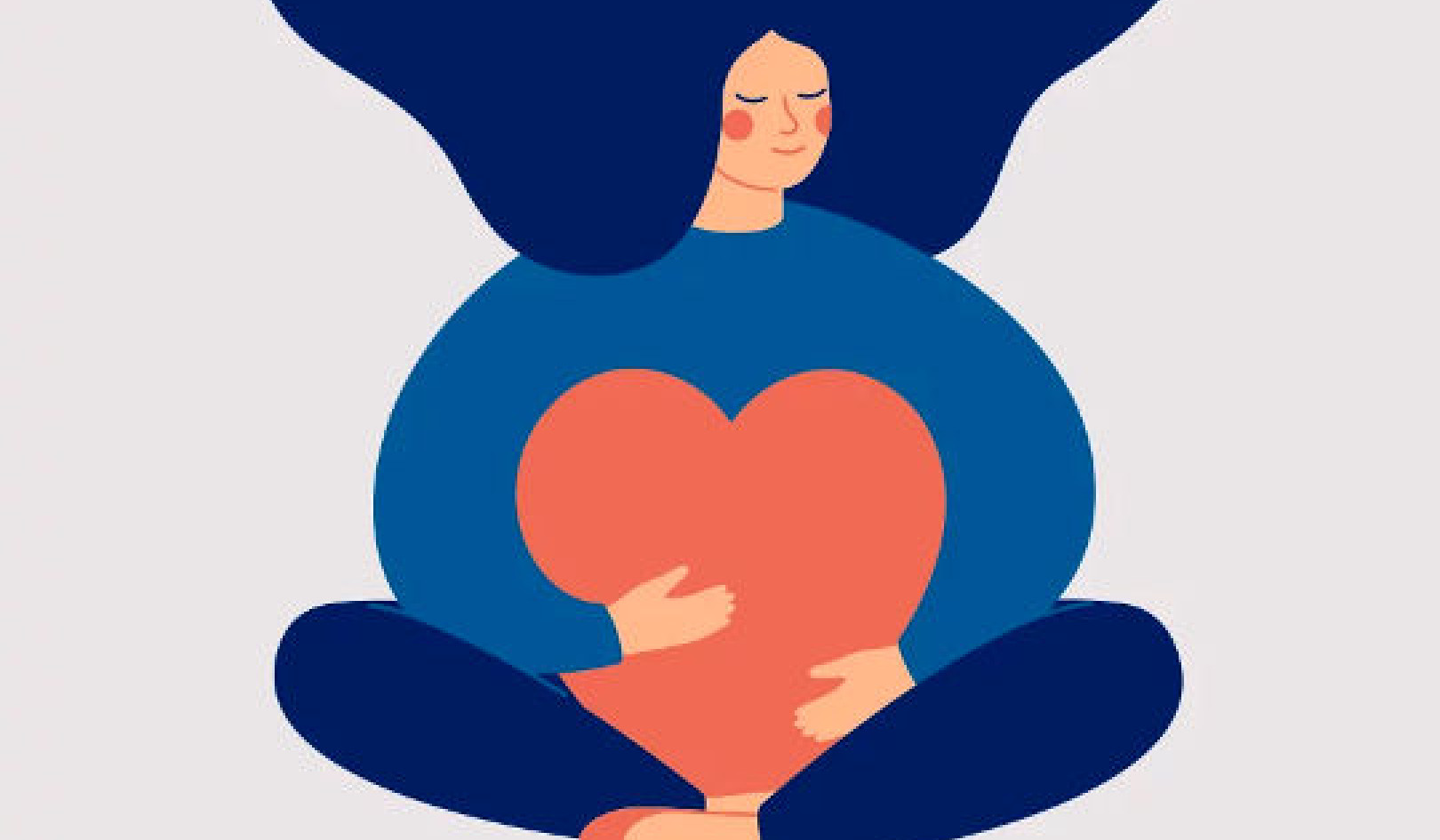恐懼繼續使我們的生活陷入困境:對核毀滅的恐懼,對氣候變化的恐懼,對顛覆性的恐懼以及對外國人的恐懼。
但最近一篇關於我們的“恐懼時代”的滾石雜誌文章 他指出,大多數美國人生活在人類歷史上最安全的最安全的地方。
它繼續:
在全球範圍內,家庭財富,長壽和教育正在增加,而暴力犯罪和極端貧困正在減少。 在美國,預期壽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我們的空氣是十年來最清潔的,儘管去年略有上升,但自1991以來,暴力犯罪一直在下降。
那麼為什麼我們仍然如此害怕?
新興技術和媒體可以發揮作用。 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一直在發揮作用。
在過去,謠言和初步的新聞報導可能會引發火災。 現在,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恐懼,時尚和幻想在整個人群中立即競爭。 有時細節的消失幾乎和它們出現的一樣快,但是對感覺,恐懼和幻想的依賴仍然存在,就像低燒一樣。
人們經常為這種情緒創造符號,這些符號是短暫的,抽象的,難以描述的。 (不用多說了 最近表情符號的崛起.)
在過去的三個世紀裡,尤其是歐洲人和美國人,已經形成了對怪物神話人物的焦慮和偏執 - 恐懼,混亂和異常的體現 - 這是我在新書中詳述的歷史, “鬧鬼”。
有四種主要類型的怪物。 但是第五個 - 一個無名的 - 可能最能代表21st世紀的焦慮。
拒絕理性
當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和科學家宣稱理性有改變世界的力量時,1700s和1800s是革命起義的時代,鼓吹了無限的未來。 通過科學推理,情感被推出了知識領域; 令人敬畏的精神受到了製服,有利於鍾表匠上帝,他將普遍規律付諸行動。
當然,人類一直都很害怕。 但是,儘管對中世紀時期惡魔和惡魔的恐懼,啟蒙運動和科學革命所帶來的變化,創造了一系列與科學和技術進步以及日益擁擠和復雜的世界相關的恐懼。
在這個政治動盪和侵略性現代化的時代,哥特式恐怖故事,鬧鬼的城堡,秘密隔間和腐爛的屍體風靡一時。 Horace Walpole,Matthew G. Lewis,Anne Radcliffe和Mary Shelley等作家的小說和故事很快成為暢銷書。 這些作家 - 以及許多其他作家 - 挖掘出一種無處不在的東西,讓名字和身體成為一種普遍的情感:恐懼。
在此期間創造的虛構怪物可分為四種類型。 每一個都對應於對進步,未來和人類實現控制世界的能力的深刻焦慮。
“來自大自然的怪物”代表了人類認為自己已經利用的力量,但卻沒有。 尼斯湖怪獸,大腳怪,金剛和哥斯拉都是這種類型的例子。 一個令人敬畏的異常,我們無法預測和爭奪,它會毫無預警地發出罷工 - 就像“大白鯊”中的鯊魚一樣。雖然明顯的靈感是真正的兇猛動物,但它們也可以被認為是自然災害的體現版本 - 颶風,地震和海嘯。
“像弗蘭肯斯坦博士的怪物一樣,創造出來的怪物是我們建造的怪物,相信我們可以控制它 - 直到它轉向我們。 他的後代是今天的機器人,機器人和機器人,他們有可能成為人類 - 並且具有威脅性。
“來自內部的怪物”是由我們自己壓抑的黑暗心理學產生的怪物,是我們平淡而無可指責的人性的另一面(想想海德先生給我們的傑基爾博士)。 當不起眼的和看似無害的年輕人變成大規模謀殺殺手或自殺式炸彈襲擊者時,“內部的怪物”已經顯露出他的臉。
“過去的怪物,”像德古拉一樣,來自一個異教徒的世界,提供了一種普通基督教的替代品,他承諾將舉行血腥盛宴,賦予不朽。 像尼采超人一樣,他代表著對普通的宗教安慰破產的恐懼,現代生活混亂的唯一答案就是確保權力。
殭屍:模糊,無名的危險
最近,我們的文化已經成為殭屍的焦點。 最近殭屍電影和故事的爆發說明了恐懼 - 雖然它可能是一種基本的人類特徵 - 呈現出特定時代和文化的形態。
殭屍 來自17th和18th世紀的野蠻加勒比奴隸種植園。 他們是不死族奴隸的無靈魂屍體,他們追踪種植園的土地 - 所以神話就這樣了。 但導演喬治羅梅羅的先鋒電影,如“死者的黎明“(1978),將這個人物概括為一個大眾消費社會的一個不假思索的成員。
“死亡黎明”的戲劇預告片。
{youtube}Yd-z5wBeFTU{/youtube}
傳統怪物(例如弗蘭肯斯坦怪物,德古拉或海德先生)之間的中心區別在於殭屍主要作為一個群體的一部分存在。 與早期的怪物不同,即使在一種宏偉的情況下,所有人都獨立存在,一個殭屍幾乎與另一個不同。
在21st世紀中,我們大腦的無意識大人物的可怕形象可能代表什麼呢? 它可以像徵我們所擔心的任何壓倒和吞沒我們的東西:流行病,全球化,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非法移民和難民。 或者它可能是不那麼有形和更具存在性的東西:在復雜的世界中喪失匿名性和個性,非個人技術的威脅使我們每個人都成為電子列表中的另一個數字。
在1918,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宣布了理性的勝利:“沒有神秘的無法估量的力量發揮作用,” 他在“科學作為職業”中寫道。 “原則上,人們可以通過計算掌握一切。”
“這個世界,”他繼續道,“對此表示不滿。”
韋伯可能有點樂觀。 是的,我們在許多方面致力於理性和分析思維。 但似乎我們需要我們的怪物和我們的結界感。
作者Leo Braudy討論了他的新書“鬧鬼”。 ![]()
{youtube}27CNwOpvzuM{/youtube}
關於作者
Leo Braudy,英國和美國文學的Leo S. Bing主席, 南加州大學 - Dornsife文學,藝術和科學學院
相關書籍:
at InnerSelf 市場和亞馬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