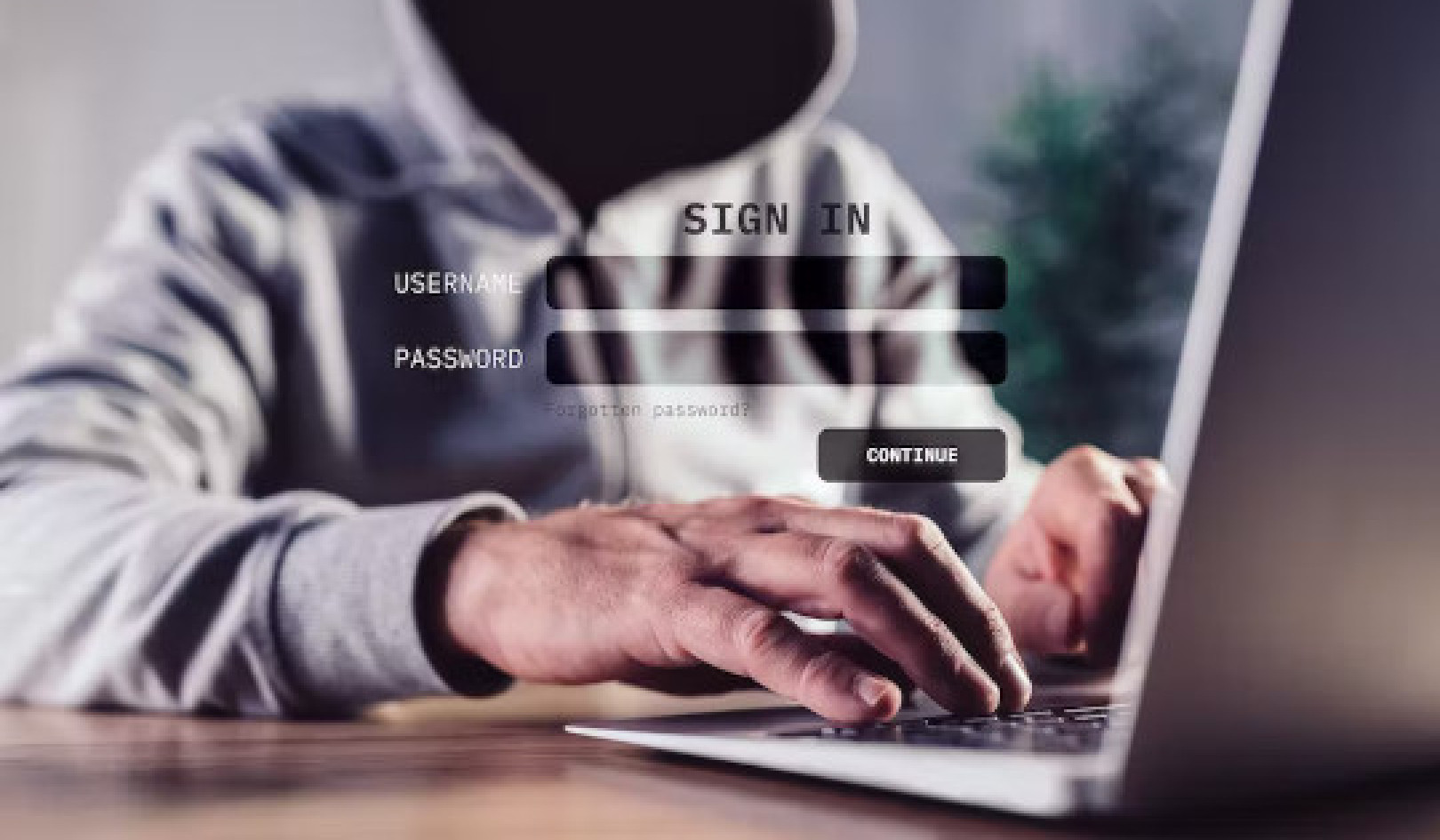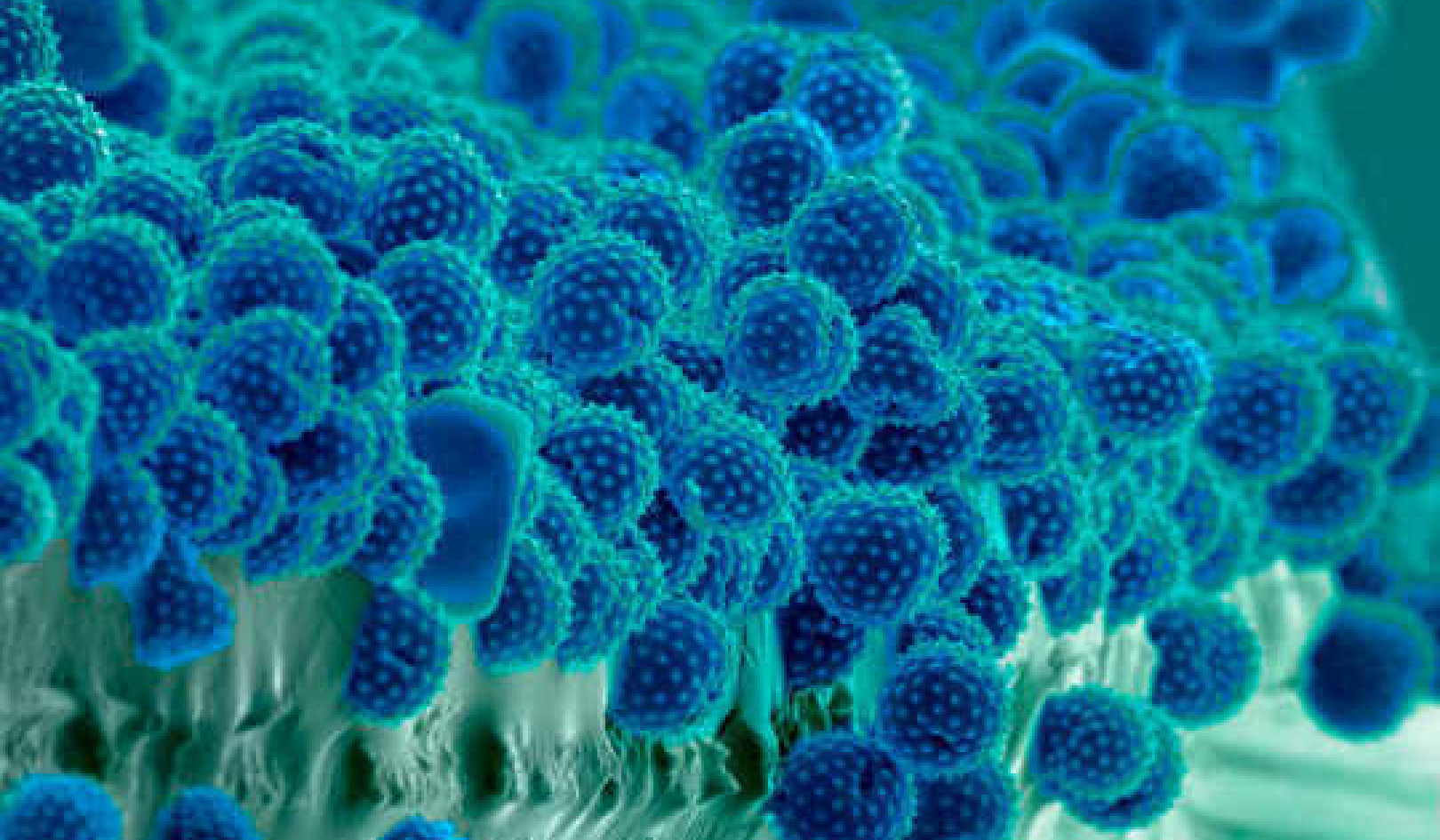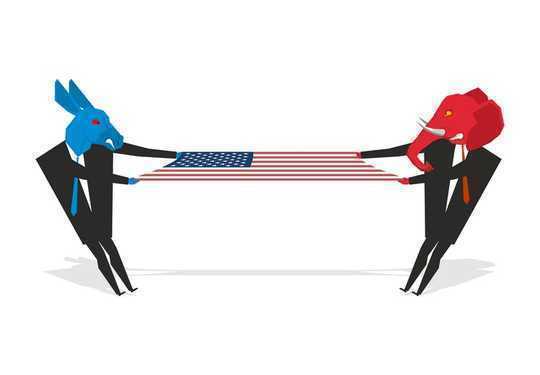 游擊隊員如何爭論公眾如何看待民主。 SHUTTERSTOCK
游擊隊員如何爭論公眾如何看待民主。 SHUTTERSTOCK
我教授和研究美國政治,我研究過美國的黨派爭論重大問題的方式。
美國歷史上充滿了一些例子,其中一個黨派方面聲稱另一方接受的某些想法有可能損害美國的國家力量或主權 - 甚至威脅到該國的存在。
但是看到今天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是不尋常的。
*特朗普總統是 與俄羅斯人合作,豐富自己。 “ 共和黨正在屏蔽他 來自問責制。
*民主黨希望通過選舉贏得選舉 重新佔領這個國家 和外國人一起 然後他們就可以了 永久改造 美國社會的種族和文化構成。
這些是由民主黨人和第二位共和黨人講述的故事版本。 讓我們拋開這些故事的優點 - 至少目前(我知道,這並不容易!)。
這些故事基本上是對不忠的指控。 如果對方實現其目標,他們預示著國家毀滅。
現在,這不僅是黨派分歧的一方,而是指責對方對美國的安全和價值觀的不忠和蔑視。 這是雙方的。 人們需要看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以證明這種黨派關係已經變得根深蒂固。
事實證明,黨派爭論的方式對美國人如何看待民主本身有影響。
那麼雙方指責對方背叛自己的國家對美國意味著什麼呢?
 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和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各自對另一方使用了世界末日的指責。 特朗普:AP / Pablo Martinez Monsivais; 佩洛西:AP / J. Scott Applewhite
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和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各自對另一方使用了世界末日的指責。 特朗普:AP / Pablo Martinez Monsivais; 佩洛西:AP / J. Scott Applewhite
黨派爭論的模式
正如我在書中討論的那樣,“擁抱異議:美國的政治暴力和黨的發展,“過去常常因為不忠誠的指控而被游擊隊員提出。
例如,在內戰期間, 原則 “每個民主黨人可能都不是叛徒,但每個叛徒都是民主黨人”是共和黨北方人都熟悉的一句話。
在冷戰期間, 共和黨人質疑民主黨人是否足夠反共 保護國家。
民主黨人經常在19th和20世紀以謹慎和防禦的方式應對這些攻擊。
民主黨人經常試圖通過將公眾辯論集中在其他問題領域來改變主題,而不是反擊。 在許多情況下,民主黨人試圖通過回應他們更民族主義的競爭對手的立場和談話點來保護自己。
同樣,在美國政治史上,當對美國忠誠的指責爆發時,通常是片面的。 “被指控”方面仍然處於守勢,抗議其對該國的承諾而沒有提出指責反訴。
這種模式傾向於鞏固民意。 一方指責,另一方否認,但雙方公開表達了對國家威脅性質的相對一致意見。
在9月11襲擊事件之後,共和黨人將民主黨人稱為 恐怖主義“軟” 並聲稱他們不願增加致力於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部隊人數“壯膽“美國的敵人。
民主黨 backpedaled 作為回應。 他們聲稱他們也致力於打擊恐怖主義,但他們會採用不同的方法來應對這一威脅。
然後雙方 - 現在
在我的研究中,我發現1790的黨派政治具有相互指責的模式,可與今天兩極分化的政治辯論相媲美。
支持喬治華盛頓總統任期的聯邦黨人 指責反對派新黨,杰斐遜共和黨人 推進法國革命事業.
傑裴遜主義共和黨人聲稱,如果聯邦黨領導人有所作為, 美國將被英國重新殖民化.
在此期間,很少有政策糾紛被認為是安全的,不受這些煽動性的懷疑。 從貿易和移民到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爭議似乎都引發了參議員們的爭議,他們的競爭對手是 在外國利益和思想的咒語下.
隨著新一代黨派報紙成為焦點,媒體慫恿了這場衝突。 上升階層的“打印機的編輯器“為政治新聞傳播建立新的黨派渠道。 這些打印機編輯通過增加對政治醜聞和公眾爭議的報導來擴大他們的報紙讀者群。 聽起來有點熟?
此外,黨派媒體對1790的許多主要政治爭議都引發了世界末日的恐懼。 黨派反對者互相指責國家的不忠。 他們說,如果對手不被阻止,共和國將遭到不可逆轉的破壞。
 1798卡通片展示了國會議員馬修里昂,杰斐遜共和黨人,羅傑格里斯沃爾德,聯邦黨人,在格里斯沃爾德侮辱里昂後在費城國會大廳裡作戰。 美國國會圖書館
1798卡通片展示了國會議員馬修里昂,杰斐遜共和黨人,羅傑格里斯沃爾德,聯邦黨人,在格里斯沃爾德侮辱里昂後在費城國會大廳裡作戰。 美國國會圖書館
游擊隊員以不同的方式設想了不可挽回的後果。 向敵對的外國勢力投降的想法是設想國家毀滅的一種方式。 1790中的黨派指責,即對方將服從英國或法國的控制,這符合這種模式。 冷戰指責 左傾的美國人接受了克里姆林宮的命令,遵循了類似的邏輯。
今天版本的外國影響力指控是最近幾個月特朗普的許多警報 批評者 特朗普總統可能是 在弗拉基米爾普京的拇指下.
當代保守派專注於不同的國家安全威脅 - 以及不同的黨派罪魁禍首。
他們認為,自由民主黨人正在努力重振國家“第三世界外國人“
這種指責通常包括提及可滲透邊界的問題。 這是相信整個或統一的國家將被外國幫派和其他人滲透“壞的hombres,“總統的話。
世界末日黨派的後果
世界末日的敘述引發了黨派爭端的風險。 他們在進行公開談判時誘使對立雙方深入挖掘。 他們還否認對手參與政治進程的合法性。
如果沒有對反對派合法性的共同理解,政治競爭者就會像敵人一樣對待彼此。 這不一定會導致政治暴力或內戰。
然而,這種辯論模式確實存在一個關鍵缺點。
由此產生的懷疑和不信任的漩渦破壞了科學和新聞等重要領域的專業人員以及法院,軍事和情報機構等機構的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專家不能完全是非政治的,公正的,超越政治鬥爭,他們可以嗎? 畢竟,如果對方的政治家不能被信任,那麼他們在其他機構中的盟友也不可能。
對於戰鬥中的游擊隊員來說,這可能並不明顯,但世界末日的敘述改變了美國人對民主本身的希望和願望。
美國人是否希望政治允許妥協和相互調整? 或者民主只不過是一個論壇,競爭對手在沙灘上畫線並互相指責?
美國人是否應該期待並接受一個政治進程,隨著時間推移會產生逐步的政 或者,共和國面臨的挑戰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沒有一個戲劇性的修正過程足以拯救這個國家?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爭論的問題的性質。 但更多還取決於美國人如何選擇辯論。![]()
關於作者
Jeffrey Selinger,政府副教授, Bowdoin College
相關書籍
at InnerSelf 市場和亞馬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