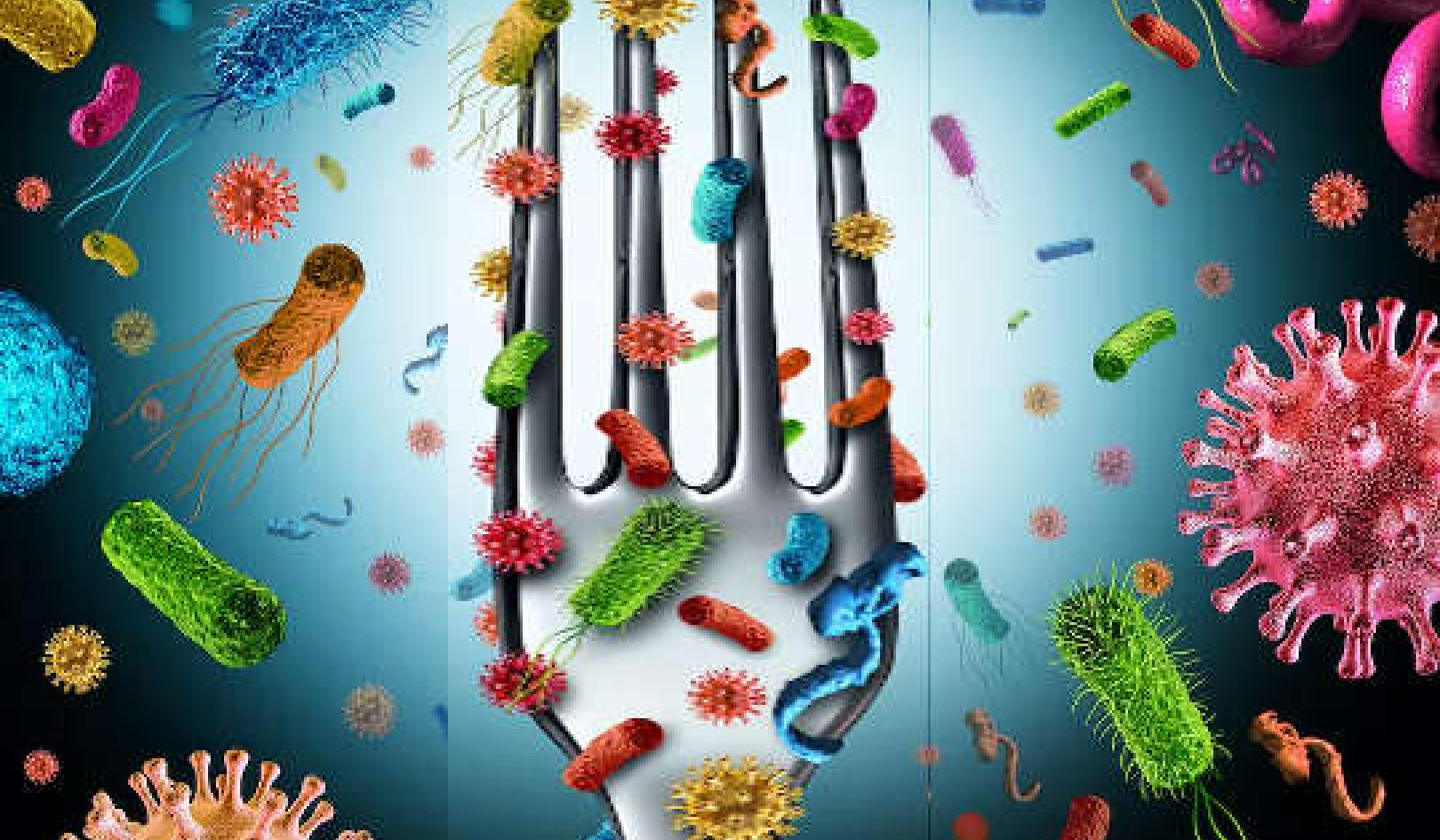《女僕的故事》系列三的女僕珍妮(Janine)。 Sophie Giraud / Channel 4
SPOILER ALERT:評論來自Margaret Atwood的小說《遺囑》中的情節和細節
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用1984編寫《女僕的故事》時, 她覺得 主要前提似乎“相當令人髮指”。 她想知道:“我是否能夠說服讀者美國經歷了一場政變,將曾經的自由民主制轉變為有字面意義的神權專政?”
時代如何改變。 現在,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部小說在集權主義,生育和控制婦女之間建立了聯繫。 紅白相間的女僕的形像已成為 抵抗文化中的象徵 限制婦女的生殖權利及其性剝削。
部分原因是電視連續劇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第三季剛剛結束。 系列一是直接根據阿特伍德的小說改編的,隨後兩年的續集延續了奧弗雷德的故事,超出了阿特伍德為她所想像的那種矛盾的結局,因為她的命運不確定。 現在,在她熱切期待的續集《遺囑》中,阿特伍德做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creative亂的創意決定,這些決定既遠離小說,又遠離電視劇。
下一代
《遺囑》的行動發生在“女僕的故事”事件發生後15年。 奧夫雷德的幽閉恐怖第一人稱敘述擴大了範圍,納入了三個敘述者的故事。 這些解說員是莉迪亞姨媽和兩名年輕女子,他們是第一部小說中姨媽中最高的,他們代表吉利德政權訓練和管理女僕。
正是這些年輕女性的身份使阿特伍德融入了電視連續劇的元素。 我們發現他們都是Offred的女兒。 一個人是阿格尼絲(Agnes),是她成為女僕後被迫放棄的女兒。 另一個叫妮可(Nicole),是小說結尾處懷有的嬰兒,並在電視節目的第二輯中生了孩子。
{vembed Y=lIOX0xI5TuA}
艾格尼絲(Agnes)是吉列德(Gilead)政權的特權女兒,她因此而長大。 妮可-以及這裡的名字選擇以及故事的各個方面,都取材於電視連續劇-已被五一國際組織從吉利德走私出去,並在加拿大長大。
這種選擇的敘述者的創造力加上時移,使阿特伍德可以做各種激動人心的事情。 她探討了成為母親的真正含義。 吉利德政權必須保留血統記錄,以避免伴隨亂倫遺傳的遺傳狀況。 阿姨將家譜信息保存在由男性一家之主組織的文件夾中,但是與生育相比,生育的不確定性總是更高的。 儘管有暗示,但我們永遠無法確定妮可的父親是誰。
但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同樣的不確定性也可以附加到母親身上嗎? 正如瑪莎(Marthas)(吉利德的家庭傭人階層)中的一位對阿格尼絲說,她發現自己認為自己的母親的人不是她的親生母親:“這取決於您對母親的意思……您的母親是那個嗎?誰生了您或最愛您的人?”當傳統的家庭結構被顛覆後,我們如何定義母親?
有所作為
這三個女性故事之間的相互作用還使我們能夠比較個人如何決定極權政權中道德行為的構成。 在《遺囑世界》中,與《女僕的故事》不同,吉利德處於後期。 它努力控制其漏水的邊界,在指揮官的上層內部存在內戰和背叛。

改變主意:莉迪亞姨媽現在正在為吉利德的倒台工作。 Sophie Giraud / Channel 4
嬰兒-有缺陷的出生-繼續出生,抵抗力不斷增強。 莉迪亞(Lydia)開始描繪吉利德(Gilead)的垮台,但回想起來,我們也得到了她關於吉利德政權建立初期合作的說法。 她摧毀吉利德的企圖是否取消了先前的合作決定? 如果她沒有倖存下來,她就不會活著來推翻這個政權,但是主人的工具能否拆除主人的房子?
抵抗運動的傷亡比比皆是。 Becka是Agnes的朋友,也是兒童遭受性虐待的倖存者,她為自己的更大利益而犧牲自己,她認為這是Gilead的淨化和更新(而不是毀滅)。 妮可(她在吉利德從事秘密行動對抵抗運動至關重要)說:“她以某種方式同意去吉利德,但從未明確表示同意”。 這本小說要求讀者考慮利用理想主義和天真性在多大程度上適合作為證明吉利德潛在毀滅終結的手段。
歷史的判斷
遺囑以吉利德研究第十三屆研討會結束–這是一個政權被摧毀之後多年的學術會議。 這與《女僕的故事》的結局相同,儘管這裡的重點有所不同。 在她的書中 在其他世界,阿特伍德(Atwood)聲稱,第一部小說的口號是為了提供“隱藏在位錯的女僕的故事中的一點烏托邦”。
但是,對於大多數原創小說的讀者來說,遇到後記的影響與樂觀主義相反。 閱讀它會減少並破壞我們對Offred敘事的情感投入,因為歷史學家們爭論著她的故事是否“真實”,而一位教授警告我們“我們在對吉利德人做出道德判斷時必須謹慎”。

反烏托邦對婦女日常壓迫的看法。 Jasper Savage / Channel 4
同一位歷史學家在結束《遺囑》的第十三屆研討會上發表了類似的評論,但在這裡他們從根本上相信證人筆錄的真實性。 奧弗雷德小說敘事狀態的後現代不確定性。 女俠的故事 可以看作是1980中期的特徵(懷疑敘事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其特徵是讓·弗朗西斯·利奧塔德(Jean-Francois Lyotard)的“對敘事的迷戀”。
現在,在2019中,Atwood用更清晰的女性故事有效性感取代了這種懷疑。 我相信,我們可以將這種重點的改變與我們所處的不同時期聯繫起來-過去和現在的所有版本具有同等地位的概念已被特朗普和其他指控“假新聞”的人明確濫用。 “。
在吉利德(Gilead),不允許女性閱讀或書寫-除非她們是姨媽。 因此,艾格尼絲努力成為一名年輕女性而素養。 她對緩慢而痛苦的識字能力的描述使我們想起了單詞和力量之間的重要聯繫,尤其是驗證女性單詞的重要性。 遺囑畢竟是見證人。![]()
關於作者
蘇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文化研究與人文學院教授,文化藝術中心主任。 利茲貝克特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