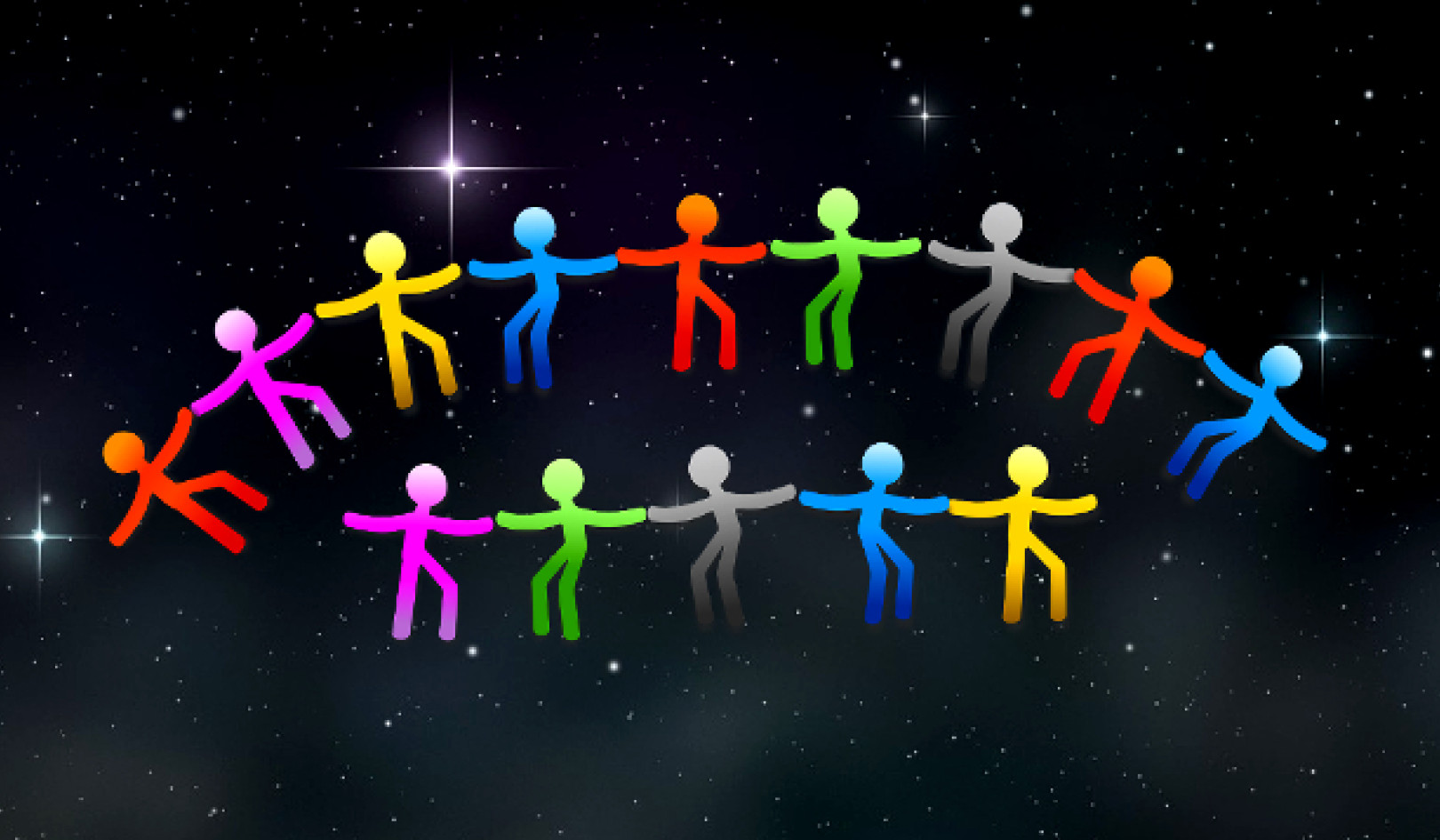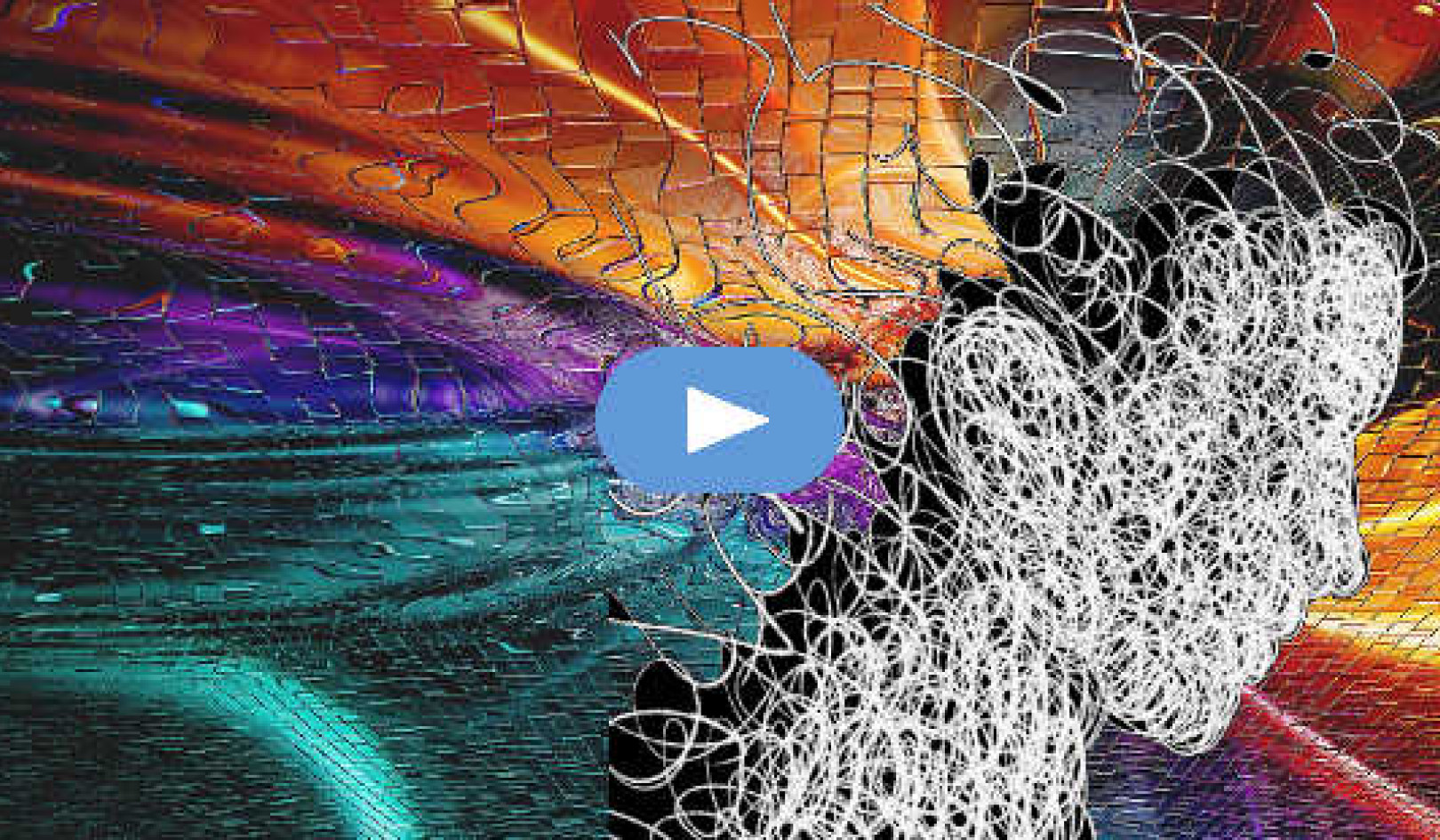當新聞打破我們最喜歡的政客的錯誤行為時,另一方不可避免地爭辯說我們手上有醜聞。 我們認為,我們對邏輯的優越把握使我們能夠推理並拒絕對方的擔憂。 ![]()
但是, 一系列三項研究 我最近發表的建議是,這些決定不僅僅是推理的結果。 相反,對政治對手的道德厭惡感強迫我們走向幫助我們團隊“獲勝”的立場。即使這意味著採取我們不同意的立場,也是如此。
簡而言之,這就是效果:想像一下,你在選舉日走進了一家冰淇淋店。 你發現這家商店裡到處都是你反對的總統候選人的支持者,你發現那個候選人的支持者在道德上是令人憎惡的。 當你到達生產線的前面時,工人告訴你所有其他顧客剛剛訂購了紅色天鵝絨 - 通常是你最喜歡的味道。
我的研究證明,當被要求下令時,你可能會有一種衝動,想要偏離你最喜歡的味道,偏向於你喜歡的那種,政治上兩極分化無關緊要的決定。
無論他們怎麼想,都要反思
要了解“敦促”的含義,有助於理解Stroop效果。 在這個經典實驗中,人們會看到一個單詞,並要求命名單詞的打印顏色。 當顏色和單詞匹配時 - 例如,“紅色”以紅色打印 - 任務很容易。 當顏色和單詞不一致時 - 例如,“紅色”以藍色打印 - 任務更難。 人們會感到意外地讀到這個詞的衝動或“衝動”。 這種衝動干擾了命名顏色的任務,應該是一項簡單的任務變得奇怪困難。
Jonathan Haidt提出的道德理論提出道德 “盲目”的人對另類觀點的看法 這樣即使考慮對方的意見也是禁忌。 考慮到這一理論,我認為道德厭惡可能是非生產性衝動的社會原因,類似於Stroop任務中的衝動。 也就是說,正如Stroop任務中的人們感受到錯誤閱讀這個詞的衝動一樣,我認為強烈的道德信仰可能會讓人感到有衝動做出決定,使他們與他們認為具有不同道德的人的距離最大化。
測試如何工作
這是我測試它的方式:
我首先讓人們做幾次Stroop試驗,讓他們知道出現錯誤的衝動是什麼感覺。
接下來,我向人們詢問了六個相當微不足道的消費者選擇問題,例如偏愛汽車顏色(森林綠與銀)或真空品牌(Hoover vs. Dirt Devil)。
這是扭曲:在回答每個問題後,參與者被告知大多數其他參與者如何回答同一個問題。 這個多數群體的身份是隨機的。 它既可以是每個人都屬於的群體(例如,美國人),也可以是更具政治色彩的群體(例如,特朗普的支持者,克林頓支持者或白人至上主義者)。
最後,我第二次向參與者展示了一組問題,並要求他們再次簡單地陳述他們之前的答案。 我還要求參與者評價他們改變答案的衝動 - 類似於在Stroop測試中出錯的衝動。
這應該是直截了當的。
沒有要求參與者評估多數答案或以任何方式重新考慮他們的意見。 儘管如此,就像在Stroop任務中感受到的干擾一樣,知道大多數反應會讓人感到有回答錯誤的衝動。
當參與者屬於多數群體時,他們報告說,當他們以前不同意多數群體時,他們會提出錯誤的衝動。 儘管被要求在一個相當微不足道的意見問題上重複他們剛才所說的話,但他們感到一種順從的衝動。
同樣,當參與者對多數群體有強烈的道德厭惡時,他們報告說,當他們與小組達成協議時,他們會提出錯誤的強烈要求。 換句話說,參與者的初步反應現在在道德上“被污染”,即使對於這些相當無關緊要的問題,他們也感到放棄這種反應並與對手保持距離的衝動。 這種衝動使得再次陳述他們的意見的微不足道的任務變得更加困難。
'蜂巢思維'和被動效應
就像美國一樣 現在在意識形態上更加分化 這些結果比歷史上任何其他觀點都闡明了政治兩極化背後的心理學兩個方面。
首先,人們可能會認為他們能夠使用他們的推理來決定最低工資增長是否會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後果。 然而,在對這個問題的任何商議思考開始之前,道德衝動可能已經推動人們不同意他們的反對者。
其次,這裡觀察到的影響可能是一個被動的過程。 參與者不希望在Stroop任務中產生錯誤的衝動,他們可能不希望在我的學習中感到與自己的觀點相矛盾的衝動。 這種衝動恰好是道德驅動的心理學的結果。
這些結果表明,將邊緣人群拉近中間的努力可能會被置若罔聞。 更樂觀的解釋是,兩極分化可能源於無意的黨派衝動。 雖然不存在導致兩極分化的道德問題,但兩極分化並不一定是由於所涉及的人的惡意。
關於作者
Randy Stein,市場營銷助理教授, 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波莫納
相關書籍
at InnerSelf 市場和亞馬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