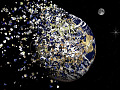雖然尚不清楚COVID-19大流行的後果,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們對支撐當代生活的系統產生了深刻的衝擊。
世界銀行 估計 到5年,全球經濟增長將收縮8%至2020%,而COVID-19將使71-100億人陷入極端貧困。 預計撒哈拉以南非洲將受到最嚴重的打擊。 在發達國家,人們對衛生,休閒,商業,教育和工作實踐進行了重組(有人說是好的),以促進專家倡導和(有時是勉強地)由政府提倡的社會疏遠形式。
我們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COVID-19所做的更改的影響。 對於某些人來說,隔離期為沈思提供了時間。 當前我們社會的結構方式如何引發此類危機? 否則我們如何組織它們? 我們如何利用這一機會應對其他緊迫的全球挑戰,例如氣候變化或種族主義?
對於其他人,包括那些被認為是脆弱或“必需的工人”的人,這樣的反映可能是直接從更加內在的感受中得知的。 是否為諸如COVID-19之類的事件做了充分的準備? 我們是否在汲取了教訓,不僅是在再次發生此類危機時如何應對這些危機,而且還從一開始就預防了這些危機? 恢復正常的目標是否足夠,還是我們應該尋求重新改造正常本身?
這些重大問題通常是由重大事件引起的。 當我們的常態意識破滅時,當我們的習慣被破壞時,我們就會更加意識到世界可能會變得不一樣。 但是人類有能力製定如此崇高的計劃嗎? 我們有能力以有意義的方式進行長期規劃嗎? 可能存在哪些障礙,也許更緊迫,我們如何克服這些障礙才能創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作為來自三個不同學科領域的專家,他們的工作考慮以各種方式參與針對意外事件(例如COVID-19)的長期計劃的能力,因此我們的工作審問了這些問題。 那麼,人類實際上是否能夠成功地為長期未來做好計劃?
牛津大學的進化心理學家羅賓·鄧巴(Robin Dunbar)認為,我們對短期計劃的痴迷可能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可能是一個可以克服的問題。 拉夫堡大學(Loughborough University)的緊急治理專家克里斯·澤布羅夫斯基(Chris Zebrowski)認為,我們缺乏準備,遠非自然而然,是當代政治和經濟制度的結果。 斯德哥爾摩大學斯德哥爾摩復原力中心的可持續發展科學家,可持續發展轉型專家Per Olsson反思瞭如何利用危機點改變未來-借鑒過去的例子,以學習如何更靈活地應對危機。未來。
我們是這樣建造的
羅賓·鄧巴
COVID-19強調了人類行為的三個關鍵方面,這些方面看似無關,但實際上源於相同的基本心理學。 其中之一是從食品到衛生紙的各種商品的搶購和庫存激增。 第二點是,當專家們警告政府多年來流行病遲早出現時,大多數州都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第三是暴露了全球化供應鏈的脆弱性。 所有這三個因素都以相同的現象為基礎:強烈傾向在短期內優先考慮以犧牲未來為代價。
眾所周知,包括人類在內的大多數動物都沒有考慮到其行為的長期後果。 經濟學家將此稱為“公益困境”。 在保護生物學中,它被稱為“偷獵者的困境”,也更通俗地說,是“公地的悲劇”。
{vembed Y=CxC161GvMPc}
如果您是伐木工人,是應該砍伐森林中的最後一棵樹還是將其保持原狀? 每個人都知道,如果靜置不動,森林最終將重新生長,整個村莊將得以生存。 但是伐木工人的困境不是明年,而是他和他的家人是否能活到明天。 對於伐木者而言,實際上從經濟上講要做的是砍伐樹木。
這是因為未來是不可預測的,但是您是否能夠實現明天是絕對確定的。 如果您今天死於飢餓,那麼未來就別無選擇。 但是如果您能度過美好的明天,那麼事情可能會有所改善。 從經濟上講,這是顯而易見的。 這部分是我們過度捕撈,森林砍伐和氣候變化的原因。
心理學家知道,支撐這一過程的是低估未來。 動物和人類 通常更喜歡 除非將來的獎勵非常大,否則現在從小的獎勵到以後的更大獎勵。 抵制這種誘惑的能力取決於額極(大腦的正上方您眼睛上方的部分),其功能之一是使我們能夠抑制這種誘惑而無需考慮後果。 正是這個小小的大腦區域,使我們(大多數人)有禮貌地將最後一塊蛋糕留在盤子上,而不是狼吞虎咽。 在靈長類動物中,大腦區域越大,它們在這類決策中的表現就越好。
我們的社會生活以及我們(和其他靈長類動物)能夠設法生活在一個大型,穩定且相互依存的社區中的事實完全取決於這種能力。 靈長類社會群體是隱性的社會契約。 為了使這些群體能夠在面對群體生存所必然產生的生態代價的情況下生存,人們必須能夠為了自己的公平利益而放棄其他一些自私的願望。 如果那沒有發生,小組將很快分裂並分散。
在人類中,無法抑制貪婪行為會很快導致資源或權力的過度不平等。 從法國大革命到法國,這可能是內亂和革命的最普遍的單一原因 香港 今天。
同樣的邏輯也支撐著經濟全球化。 通過將生產轉移到生產成本較低的其他地方,本土工業可以降低成本。 問題在於,這是由於增加了社會保障支出來支付現在家庭工人中多餘的僱員,直到他們找到替代就業為止,這對社區造成了損失。 這是一個隱性成本:生產者沒有註意到(他們可以賣得比以前便宜的多),而購物者沒有註意到(他們可以買到便宜的)。
有一個簡單的規模問題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的 自然的社會世界 規模很小,幾乎沒有村莊大小。 一旦社區規模擴大,我們的興趣就會從更廣泛的社區轉向對自身利益的關注。 社會錯綜複雜,但正如所有歷史帝國所發現的那樣,社會變成了一個不穩定的,越來越脆弱的組織,有繼續分裂的危險。
企業提供了這些影響的小規模示例。 富時100指數中公司的平均壽命為 急劇下降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四分之三在短短30年內消失了。 倖存下來的公司是具有遠見的公司,對快速致富的策略不感興趣,這些策略不會使投資者獲得最大回報,也沒有社會效益。 那些已經滅絕的企業主要是那些追求短期戰略的企業,或者由於規模龐大而缺乏適應性結構靈活性的企業(請考慮度假經營者)。 托馬斯庫克).
 我們自然的社會世界幾乎沒有村莊大小。 羅伯·柯倫/ Unsplash, FAL
我們自然的社會世界幾乎沒有村莊大小。 羅伯·柯倫/ Unsplash, FAL
最終,很多問題都會縮小。 一旦社區超過一定規模,其大多數成員就會變得陌生:我們失去了對他人的個人和社會所代表的公共項目的承諾感。
COVID-19可能會提醒許多社會,它們需要重新考慮其政治和經濟結構,使其成為更接近其成員的本地化形式。 當然,這些肯定需要合併聯邦上層建築,但是關鍵是自治社區一級的政府,公民認為他們在事情的運作方式上有個人利益。
政治的力量
克里斯·澤布羅夫斯基
就規模和規模而言,它沒有比里多運河大得多。 伸展 全長202公里,加拿大的里多運河被視為19世紀最偉大的工程壯舉之一。 該運河系統於1832年開放,旨在作為通往連接蒙特利爾和金斯敦海軍基地的聖勞倫斯河重要河段的替代補給路線。
該項目的推動力是在美國,英國及其盟國之間發生戰爭之後,與美國人繼續敵對的威脅。 來自1812-1815。 儘管運河永遠不需要用於預期的目的(儘管成本高昂),但這只是人類的機智與巨大的公共投資結合在一起的一個例子,以應對不確定的未來威脅。
 裡多運河的一部分,托馬斯·伯羅斯(Thomas Burrowes),1845年。 ©安大略省檔案館
裡多運河的一部分,托馬斯·伯羅斯(Thomas Burrowes),1845年。 ©安大略省檔案館
“折現未來”很可能是一個習慣。 但是我不認為這是我們如何 大腦是有線的 或我們靈長類祖先的悠久遺產。 我們對短期主義的傾向已經社會化。 這是我們今天在社會和政治上組織起來的方式的結果。
企業會優先考慮短期利潤而不是長期利潤,因為它吸引股東和貸方。 政治家不贊成長期項目,而希望採用快速解決方案來保證即時結果,這種解決方案可以在每四年發布的競選文獻中找到。
同時,我們周圍有許多風險管理工具的例子,這些工具非常複雜,而且往往資金充足。 重大的公共工程項目,重要的社會保障體系,龐大的軍事組織,複雜的金融工具以及精心設計的保險政策,支持了我們當代的生活方式,證明了我們有能力為未來作計劃和做好準備的能力。
近幾個月來,公眾對應急準備和響應系統在管理COVID-19危機中的至關重要性。 這些是高度複雜的系統,它們使用視線掃描,風險記錄,備災演習和多種其他專業方法來識別和計劃未來的緊急事件。 此類措施可確保我們為將來的事件做好準備,即使我們不確定何時(或是否)會實現這些事件。
雖然我們無法預測COVID-19的爆發規模,但亞洲先前的冠狀病毒爆發意味著我們知道 一個潛在可能。 世界衛生組織(WHO)已警告過 國際流感大流行 多年了。 在英國,2016年國家防災項目“運動天鵝座”明確表明: 該國缺乏能力 充分應對大規模公共衛生突發事件。 危險已經明確識別。 眾所周知,為這場災難做準備。 缺乏在這些重要係統上提供足夠投資的政治意願。
在許多西方國家,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以及緊縮的邏輯)導致許多關鍵服務(包括緊急情況準備)的資金被削減,這是我們安全與保障所依賴的。 這與包括中國,新西蘭,韓國和越南在內的國家形成鮮明對比,這些國家對準備和響應的承諾確保了 快速抑制 疾病及其對生命和經濟的破壞力降至最低。
儘管這樣的診斷可能首先看起來很暗淡,但是有充分的理由在其中找到希望。 如果造成短期主義的原因是我們組織方式的產物,那麼我們就有機會重組自己以解決這些問題。
最近的研究表明,公眾不僅認識到氣候變化的風險,而且認識到 要求緊急行動 採取措施避免這種生存危機。 我們不能讓COVID-19的死與毀滅白費。 在這場悲劇發生後,我們必須準備徹底地重新考慮我們如何組織自己的社會,並準備採取雄心勃勃的行動來確保我們物種的安全和可持續性。
我們不僅具有應對未來大流行的能力,而且還具有應對更大範圍(也許並非無關)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各種威脅將要求我們在面對未來威脅時行使人類的遠見和審慎能力。 這樣做並非超出我們範圍。
如何改變世界
佩爾·奧爾森
儘管在流行病分析中出現了短期主義和結構性問題,但那些關注長期研究的人一直認為這是變革的時候了。
COVID-19大流行導致許多人爭論說這是 千載難逢的時刻 進行轉化。 這些作家說,政府的回應必須推動 深遠 與能源和糧食系統有關的經濟和社會變革,否則我們將來將容易受到更多危機的影響。 有些人進一步聲稱 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一個更加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而不再痴迷於增長和消費。 但是同時轉換多個系統並非易事,值得更好地了解我們對轉換和危機的了解。
歷史向我們表明,危機確實確實創造了獨特的變革機會。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73年的石油危機如何使荷蘭的汽車社會過渡為自行車國家。 在能源危機之前, 對汽車越來越反對,並出現了一場社會運動,以應對日益擁擠的城市和與交通有關的死亡人數,特別是兒童的死亡人數。
 騎自行車是荷蘭的主要交通方式。 傑斯與阿芙森/未飛濺, FAL
騎自行車是荷蘭的主要交通方式。 傑斯與阿芙森/未飛濺, FAL
另一個例子是黑死病,這是14世紀席捲亞洲,非洲和歐洲的瘟疫。 這導致了 廢除封建制度 以及加強西歐的農民權利。
但是,儘管可以從危機中產生積極的(大規模)社會變革,但後果並不總是更好,更可持續或更公正,而且有時出現的變革因環境而異。
例如,2004年印度洋地震和海嘯影響了亞洲運行時間最長的斯里蘭卡和印度尼西亞亞齊省的兩次叛亂 非常不同。 在前者中,斯里蘭卡政府與分離主義的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之間的武裝衝突由於自然災害而深化和加劇。 同時,在亞齊省,印度尼西亞政府與分離主義者達成了歷史性的和平協議。
其中一些差異可以用衝突的悠久歷史來解釋。 但是,不同群體準備進一步推進議程,應對危機本身的方式以及在海嘯發生後的行動和策略也有重要作用。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變革的機會可以被自私自利的運動抓住,因此可以加速非民主傾向。 不希望提高公平性和可持續性的團體之間可以進一步鞏固權力。 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 在菲律賓和匈牙利等地。
由於有許多人呼籲變革,因此討論的餘地是變革的規模,速度和質量至關重要。 更重要的是,成功應對這種重大變化所需的特定功能。
人們通常會混淆哪些行動實際上會有所作為,現在應該做什麼以及由誰來做。 這樣做的風險是,錯過了由危機創造的機會,而憑藉最好的意圖和創新的承諾,努力只會回到危機前的狀態,或者略有改善,甚至導致危機。根本更糟。
例如,有些時候抓住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改變金融部門,但是最強大的力量將系統推回了類似於崩潰前的狀態。
造成不平等,不安全和不可持續實踐的系統不容易轉變。 顧名思義,轉型需要在多個方面進行根本性的改變,例如權力,資源流動,角色和慣例。 這些轉變必鬚髮生在社會的不同層面上,從實踐和行為,到規章制度,再到價值觀和世界觀。 這涉及到改變人類之間的關係,也深刻地改變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我們看到,在COVID-19期間,現在(至少在原則上)致力於此類變化的努力,曾經被視為激進思想的想法現在已由許多不同的小組採用。 在歐洲,綠色復甦的想法正在增長。 阿姆斯特丹市正在考慮實施 甜甜圈經濟學 –旨在提供生態和人類福祉的經濟體系; 和 普遍基本收入 正在西班牙推出。 所有這些都在COVID-19危機之前就已經存在,並且在某些情況下已經進行了試點,但是這種大流行使火箭助推器成為了現實。
因此,對於那些尋求利用這次機會創造改變以確保我們社會的長期健康,公平和可持續性的人,有一些重要的考慮因素。 剖析危機的根源並相應地調整行動至關重要。 此類評估應包括以下問題:發生何種類型的多重危機,相互作用的危機,“現狀”的哪些部分真正崩潰,哪些部分仍然牢牢存在,誰受所有這些變化的影響。 要做的另一件事是確定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準備就緒”的試點實驗。
處理不平等和 包括邊緣化的聲音 避免轉型過程被一組特定的價值觀和利益所支配和選擇。 這也意味著尊重並與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衝突的競爭價值觀合作。
我們如何組織努力將定義未來幾十年的系統。 危機可以是機遇,但前提是要明智地應對危機。
關於作者
羅賓·鄧巴(Robin Dunbar),實驗心理學系進化心理學教授, 牛津大學; 政治與國際關係講師Chris Zebrowski 拉夫堡大學以及斯德哥爾摩彈性中心研究員Per Olsson, Stockholm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