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條紋巴士
作者:洛倫佐·W·米拉姆
T這是我二十年前讀過的一本偉大的書。這是一位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性治療師的作品。她正在寫她所謂的「性少數」。她說,最大的性少數群體是永久殘疾的人,尤其是那些住在醫院和療養院的人。她說,這些地方的道德規範規定我們不應該有任何性自由:沒有愛,沒有激情,沒有出口。
S前任和殘疾人士?這是雙重的憂慮。身心障礙者不應該想到、想要、需要、能夠發生性行為。這在術語上和理解上都是矛盾的。我們已經成為社會的太監了。
B但是(正如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所說),我們要自擔風險來扼殺性。它可以被引導和重定向——但是當我們試圖完全阻止它的力量時,我們就會在內部和外部創造出怪物。
I 看到四肢癱瘓的人、多發性硬化症患者、老脊髓灰質炎患者、盲人、心臟病患者,將他們的性行為放在次要位置,或者更糟的是,試圖完全撲滅火焰。因此,性不再是一個問題(他們認為)。缺乏性成為一種偏好,對吧?
性回憶
A然後我想起了瑞典關於性少數的精彩故事。寫這篇文章的醫生想要設置這些公共汽車,這些馬戲團公共汽車。他們會隨身攜帶什麼?妓女!
T妓女會被送往大醫院。你認識他們,你很了解他們——那些單調、黑暗的醫院和療養院,有著單調的橄欖綠牆壁,還有它們的氣味——腐爛和悲傷的氣味——和乾涸的悲傷我們都知道這樣的地方。
T妓女會進來,十幾個,十五個,兩打。每個人都會被分配一個或兩個病人去愛、給予愛、擁抱。對一些病人來說,這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的第一次(我幾乎寫了囚犯)。對他們中的一些人來說,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A對於那些無法站起來的人還是對於那些在下面沒有感覺的人?操縱、視覺刺激、話語、耳邊低語的話語、手刺激身體的任何部位、任何愛的感覺被轉移的部位。 (它們已經移到了某個地方;它們總是這樣做:到脖子、耳垂、嘴唇、肩膀;腋窩:他們說那是身體最性感的部位之一。)到處都是手——還有甜蜜的低語。
A 愛情的狂歡節。每個月,紅白條紋、黃輪的巴士都會停在城裡的療養院:“慢性病患者”、“病人”,受到專業人士的關懷。
W護理師會感到憤怒嗎?當然。政客們?嚇壞了!機構?社論會飛起來。你聽到他們在獸醫院做什麼了嗎?他們讓——(他們怎麼稱呼他們?)“慢性病”,他們讓他們在病房裡養妓女!你能相信嗎?妓女用納稅人的錢付錢。
A每個人都會感到震驚、憤怒,試圖阻止它……這個、這個……發生在我們的倉庫裡,為永久殘疾人服務。每個人……每個人……除了查理。
查理呢?
C哈莉在退伍軍人之家已經二十年了──不,讓我們想想,現在已經二十二年了。他只是躺在那裡,看電視,抽煙。勤務兵給他餵食,給他清理。他沒有家人──沒有人來看他。有一個叔叔,什麼時候回來的? 1970 年? 1972 年?老傢伙終於死了或只是走了,再也沒有見過
C哈莉有時會想起那時的日子,當時他十八歲,在他(或任何人)聽說越南之前。他那麼年輕,渾身都是尿和醋——和他的女朋友珍妮出去,有時在深夜,她會抱著他,坐在那輛舊轎跑車(一輛59年的普利茅斯,棕褐色,有擋泥板裙)的前面。他們離得如此之近,他以為自己要爆炸了……那是在越南和地雷之前。他們告訴他有關地雷的事,但他從來沒有猜到,從來沒有猜到地雷會對他的身體、雙腿、下面溫柔的部分、對靈魂造成什麼影響。
妓女...會被分配一個或兩個病人
- 愛,給予愛,持有。
He從來沒有猜到過。我們這些孩子是如此天真,如此非常天真……從那時起……發生了什麼? ……自 1965 年以來,二十多年來,查理一直在退伍軍人醫院(兩年半,十二年)行動;其中成功的不多)。然後在療養院這裡。他的家人?他們剛剛死掉了。就像他的朋友一樣。死了,或者消失了。現在有勤務兵、助手和其他病人……還有電視……電視上的射擊聲——火箭聲、炸彈聲,當他聽到時,仍然讓他有些震動。電視傳來戰爭的聲音,還有病房裡的喧鬧聲,餐盤上來了。有時他會吃東西,但大多數時候他只是躺在那裡,抽著駱駝煙。而除了護士之外,沒有人讓他想起珍妮,想起二十年前的時光…
E每個人都認為「妓女巴士」是一個醜聞。城裡的每個人。除了查理——以及他在病房裡的幾個夥伴。因為有件事他已經二十年不知道了。女人的觸碰……看著她靠近他。她的手。她的頭髮就這樣掉下來了……已經二十年了。 「天啊,」他想:「多麼美麗啊……她的手,還有她的眼睛。對我來說……」每個人都反對。除了查理…和他的幾個朋友,在病房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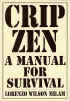 本文摘自《克里普禪”,Lorenzo W. Milam 著,1993 年,經出版商 Mho & Mho Press 許可重印,郵政信箱 3490,聖地亞哥,CA 92163。
本文摘自《克里普禪”,Lorenzo W. Milam 著,1993 年,經出版商 Mho & Mho Press 許可重印,郵政信箱 3490,聖地亞哥,CA 92163。
信息/訂單簿
關於作者
洛倫佐·米拉姆被稱為“倖存者的倖存者”。他已殘疾四十多年,是九本書的作者,其中包括兩本小說。他最新的旅遊書《The Blob That Ate Oaxaca》獲得 1992 年普立茲獎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