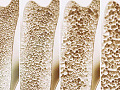無人機。 Gregor Hartl / Flickr。 保留一些權利。
無人機。 Gregor Hartl / Flickr。 保留一些權利。
一種新的戰爭:城市空間如何成為新的戰場,智力與軍事,戰爭與和平之間的區別正變得越來越成問題。
在18世紀後期所謂的製度建設 圓形監獄,由英國人Jeremy Bentham設計。 目的是獲得“心靈的力量”。[1] 自設計以來 圓形監獄 作為監獄建設的靈感來源,因為它允許觀察人們,而不知道他們是否被觀察。 受到監視的持續不確定性可以改變行為。
城市正在成為我們日益增長的城市世界的新戰場
全景凝視 不僅限於監獄。 它存在於從工廠到商店的各種公共場所,特別是人們被分組,計數,檢查和標準化的場所。[2] 雖然 圓形監獄 關注個人的監視, panspectron 旨在觀察整個人口,每個人和所有人都在一直受到監視。 [3]
政府使用這種紀律手段來加強其主權。 在這個日益城市化的世界中,這些項目表明了民族國家有興趣將高科技全知的軍事思想運用到城市公民社會中。 到20世紀末,10%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 他們大多數生活在全球北部的大都市。 今天,城市人口幾乎佔世界人口的50%,主要居住在全球南部的大城市。[4]
這種快速的城市化非常重要;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如何組織起來對人類至關重要。[5] 雖然西方城市正致力於提高安全水平,但發展中國家的城市面臨著更高的暴力和犯罪率以及軍事化的加劇。[6] 因此,保持對人口和人民運動的控制和監視,使國家當局能夠更好地為暴力和戰爭做好準備。 在西方社會的全球化中,流動性對權力和發展的重要性日益增加。[7] 雖然現代權力需要限制和界定人們的運動,但它們也需要人員的運動才能監測和分析它們。[8]
21st世紀的戰場
由於認為全球城市化正在削弱帝國民族國家的紀律和殺戮能力,美國和以色列等國家正在從根本上重新思考他們在城市中發動戰爭的方式。[9] 從全球南方的貧民窟到西方富裕的金融中心,城市成為我們日益增長的城市世界的新戰場。
城市成為我們日益增長的城市世界的新戰場
例如,加沙是人口密集的360平方公里區域,人口為1.7百萬。 自從2007以來,加沙一直由哈馬斯控制,與其他巴勒斯坦領土完全分開。 在哈馬斯控制之後,以色列開始對加沙完全關閉土地,並創建了世界上最大的監獄。[10] 進出的唯一方式是通過連接加沙和埃及的隧道。 這種關閉迫使以色列更多地投資於監視技術,因為他們對線人的訪問變得如此受限制,以至於或多或少都不可能。[11] 因此,加沙成為新的監測和人口控制技術的試驗場。 在加沙和西岸使用的這種技術包括生物識別系統,面部識別和使用監視氣球甚至無人機,使安全部門能夠控制所有通信。[12]
以色列航空安全發明的種族和行為特徵已成為世界各地機場的標準。 9/11之後,對國土安全相關技術的需求迅速增長,以色列成為最大的供應國。 以色列控制著70%的無人機市場,並且是邊界監視控制的領導者。 此外,以色列為世界提供了有關航空安全系統和協議,圍欄和機槍系統的先進技術。[13]
美國和以色列之間的牢固關係為該國提供了進入歐洲,中國,印度等市場的機會,從而使這項技術成為許多西方國家的新標準。 例如,生物識別護照是世界上唯一有效的護照,面部識別甚至被Facebook使用。
加沙和以色列之間的邊界經歷了大規模的重建。 它旨在引導參賽者進入一系列身份識別艙。 每間客艙都配有自己的生物識別身份系統,可將參賽者與身份證上的數據進行比較。[14] 顯然,戰場上使用的監視技術現在被用於民用控制。 空間政治在空間產生的過程中產生了鬥爭。
反恐戰爭
政治比運動本身更重要的是移動或留在一個地方的權利。[15] 當人口對這種技術進行規範化時,它就成為國家政策的基礎。 此外,監視和控制技術的合法化通常是在“反恐戰爭”的藉口下使用,以及需要保護國家免受內部和外部威脅。 這導致了對新技術的利用,以加強國家的合法性並加深其控制。[16]
監視和控制技術的合法化通常是在'反恐戰爭'
以色列使用的技術和技術多年來一直激勵著美國軍隊。 現在,諸如混合實時高科技監視,狙擊手全面報導以及炸毀城市新街道和通道等技術,為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奠定了基礎。[17]
記住對費盧杰市的襲擊,這座城市是抵抗在伊拉克建立美國友好政權的象徵性中心 - 儘管未經證實費盧杰實際上是關鍵伊斯蘭抵抗運動的基地Abu Musab al-Zarqawi的領導人。[18] 在這裡,美國軍隊參加了人口稠密的城市中伊拉克戰爭中最沉重的戰鬥。 美國的宣傳活動使費盧杰的襲擊合法化,將伊拉克戰爭的所有傷亡描述為“恐怖分子”,“薩達姆保皇黨”或“基地組織戰士”。[19]
這種宣傳依賴於想像的地理位置,這些地理位置操縱著'反恐戰爭' 並以非常有力的方式構建伊斯蘭城市的地方。[20] 就像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軍事言論一樣,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被視為邪惡的“兒童”。
因此, 他者化 使城市及其居民遠離任何文明概念的工作,並支持軍隊大規模濫用武力的合法化。
對城市空間的攻擊
城市生活的典型特徵是,城市空間應該鼓勵人們在沒有真正“了解”彼此的情況下共同生活。[21] 社會需要陌生人聚集在一起以便彼此了解的地方,但這種公共領域的理想已被私有化和電視和手機等技術“攻擊”。[22] 這導致人們在社交上自我隔離,越來越多地從公共場所消失到他們的私人領域,使當局能夠更容易地實施他們的安全措施。
個人對技術的大量使用以及對其私人領域的限制,將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效果脫鉤,城市空間應該提供。 在想像的地理位置,敵人被構建為對抗不可知的戰爭中的休眠恐怖分子 其他類.[23]
如今,最簡單的技術可以用來對付我們,我們也不會意識到這一點
如今,最簡單的技術可以用來對付我們,我們甚至都不會意識到這一點。 例如, 普通人 無人機可以很容易地在線購買。 大多數這些玩具無人機已經配備了攝像頭,可以通過智能手機進行駕駛。 如果一個潛在的恐怖分子推進這些玩具並建造一個裝有自製炸彈的更複雜的版本,從而產生一種新的恐怖程度,即將到來?[24]
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致命的潛力依賴於最簡單的技術,只是反作用。 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技術,例如Web 2.0,具有其全方位的方面,可用於映射社交關係並利用特定主題。[25]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自由地為這個框架做出貢獻,因為我們不想錯過新技術為我們提供的舒適。
在21世紀,沒有社交媒體和互聯網幾乎不可能生活
在21世紀,沒有社交媒體和互聯網幾乎是不可能生活的,尤其是在現代西方國家。 情報機構也使用這種信息來繪製政治活動家的社交網絡。 例如,在阿拉伯之春期間,有關中東示威活動的許多信息都是通過社交媒體網絡免費在線收集的。[26] 隨後,幫助革命的技術也可以用來追踪和逮捕同樣的活動家。
隨著w的開始反恐 其中涉及的技術,反全球化抗議,社會運動和示威都面臨著同樣的垂直電子和軍事力量和監視,美國軍事戰略組織阿富汗也採用了這種方式。[27]
戰爭長期以來一直是國家或城市的技術基礎設施。 9 / 11的恐怖襲擊以及倫敦和馬德里的地下爆炸事件證明了這一點。 在過去,戰爭在戰場上進行。 主要目標是提高大規模軍隊,但不針對平民。 9 / 11已經產生了一種新的戰爭,其中w反恐 現在依賴於城市空間的辯證結構。
歷史上,現代主權在1648的威斯特伐利亞和平條約中形成,這也是我們今天所知的國際體系的起點。 這種公共暴力的重組和國家對暴力的壟斷是確保國家公民日常安全免受隨意武力行為的核心工具。[28] 恐怖襲擊破壞了這種壟斷,給人們帶來了恐懼。 它們還導致更多的監視和更嚴格的國內政策,因為恐怖分子和反叛分子往往被視為人口不足。
新軍事都市主義
現在,現代國家必須證明它可以保護其所有公民隨時隨地遭受政治暴力。 人口習慣於政治暴力的次數越少,恐怖主義行為發生後公眾的震驚就會越大。 為了滿足這一需求,民族國家實施了新的安全措施,以控制和監視其人口並預測未來的恐怖襲擊。 為了確定這些敵人,已經在伊拉克和以色列城市中使用的技術在現代西方城市中得到了應用。
人口越少習慣於政治暴力,恐怖主義行為發生後的公眾衝擊就越大
這種新的軍事都市主義建立在這樣一個中心思想上:在西方城市和世界的新領域,如城市景觀和人們的日常生活空間中,技術用於追踪和瞄准人的軍事戰術被永久地實施。阿富汗和伊拉克。[29] 其中大部分都是因為擔心恐怖分子和叛亂分子受益於西方國家提供的匿名性,而這些國家將利用和瞄準城市的技術基礎設施。 紐約,馬德里和孟買的襲擊以及對巴格達,加沙,貝魯特等地的軍事攻擊支持了這一新戰爭引發全球暴力事件的假設。[30]
換句話說,在這個所謂的 低強度衝突 城市空間正在成為新的戰場,智力與軍事,戰爭與和平以及地方和全球行動之間的司法和作戰區別正變得越來越成問題。[31]
因此,各州將繼續花費資源將好人和有威脅的人分開。 新的法律基礎將取決於個人,地點和行為的概況,而不是人權。 學者甚至已經診斷出典型的殖民地技術重新進入城市管理。 以色列制定的射殺政策現在已被歐洲和美國的警察部隊採用。 與此同時,西方城市更具侵略性和軍事化的警察正在使用相同的武器控制公眾示威和抗議活動,就像以色列軍隊在加沙一樣。[32]
關於作者
Feodora Hamza在德國弗賴堡學習伊斯蘭研究,並在英國蘭卡斯特大學完成了她的宗教和衝突碩士學位。 她住在海牙。
相關書籍:
at InnerSelf 市場和亞馬遜
Refrences
[1] Dahan,Michael:加沙地帶作為Panopticon和Panspectron:紀律和懲罰社會,p。 2
[2] Innokinetics: http://innokinetics.com/how-can-we-use-the-panopticum-as-an-interesting-metaphor-for-innovation-processes/ 下載:17.01.2016
[3] 同上。 p.26
[4] 格雷厄姆,斯蒂芬:圍城之城:新軍事都市主義,p.2
[5] 同上。 頁。 4
[6] 格雷厄姆,斯蒂芬:圍城之城:新軍事都市主義,p.4
[7] 里德,朱利安:建築,基地組織和世界貿易中心,重新思考戰爭,現代性和空間之間的關係9 / 11之後,p。 402
[8] 同上。
[9] 格雷厄姆,斯蒂芬:記住費盧杰:妖魔化地方,構建暴行,p。 2
[10] Dahan,Michael:加沙地帶作為Panopticon和Panspectron:紀律和懲罰社會p。 29
[11] 同上。
[12] 達漢,邁克爾:加沙地帶作為Panopticon和Panspectron:懲戒和懲罰社會p.28
[13] 同上。 p.32
[14] 同上。
[15] Mobilites的地理位置 182
[16] Chamayou,Gregoire:無人機理論,p.27-28
[17] 格雷厄姆,斯蒂芬:記住費盧杰:妖魔化地方,構建暴行p.2
[18] 同上。 頁。 3
[19] 同上。 頁。 4
[20] 同上。
[21] De Waal,Martijn:有感知的城市的城市文化:從事物的互聯網到事物的公共領域,p。 192
[22] 同上。
[23] 格雷厄姆,斯蒂芬:城市和“反恐戰爭”,p.5
[24] 施密特,埃里克; 科恩,賈里德:新數字時代,p。 152 - 153
[25] 達漢,邁克爾:加沙地帶作為Panopticon和Panspectron:懲戒和懲罰社會,p.27
[26] 同上。
[27] 達漢,邁克爾:加沙地帶作為Panopticon和Panspectron:懲戒和懲罰社會,p.27
[28] Kössler,Reinhart:現代民族國家和暴力政權:對當前形勢的反思
[29] 格雷厄姆,斯蒂芬:圍城之城:新軍事都市主義,十四
[30] 同上。
[31] 同上。
[32] 同上。 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