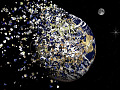專家知識是否應限於在民主國家中提供僕人角色,還是提升到合作夥伴的角色?
我們大多數人都對這個問題抱有矛盾心理。 我們希望專家對民主審議和決策的投入,但不是主導討論。 因此,我們大多數人都被尋求建立“恰到好處”專業知識的Goldilocks原則所誘惑。
但是,不清楚僕人或伴侶角色是否提供了實現金發姑娘原則的最佳機會。 在我們的民粹主義時代,許多人被僕人的角色所吸引,因為它承諾在專業知識和民主之間保持一種不透水的劃分,從而保護民主免受技術統治。
但我建議只有合作夥伴角色才能真正實現Goldilocks“足夠”專業知識的可用性原則。
我們對專家很矛盾
我們都很難知道多少“足夠”的專業知識的一個原因是我們都不是完美的。 我們傾向於從厭惡到喜歡的專家轉變為欣賞技術技能而非社會應用的中間立場。
考慮三個關於民主專業知識的故事,說明這種矛盾心理:全球核辯論,南澳大利亞核燃料循環皇家委員會以及南澳大利亞風暴引發的全州停電的後果。
核辯論已經被如此感染 技術專家 專家推理即使 氣候科學家 很容易吞下感覺良好的核丸。
核專家堅持認為核電可能是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一種廉價而簡單的解決方案 - 但否認更廣泛的社會關切,即核電是 社會投資回報率低.
然而,爭論仍在繼續,因為親核專家 公眾關注的邊緣化, 櫻桃挑選他們的數據,解散了 真實的狀態 一個垂死的核工業,暗中破壞了公民的民主影響。
此外,那個呻吟的核工業需要埋葬其核廢料問題或親吻政治家或會計師簽署新反應堆的任何希望。
而技術和技術 深層地質處置 即使最好的努力(加拿大的)已陷入困境,他的雄心壯志也是令人欽佩的,也可能是勇敢的。 顛覆民主討論的歷史.
南澳大利亞核燃料循環皇家委員會 2016繼承了同樣的技術專家。 委員會 總結報告 建議追求核反應堆和廢物處理,因為前者可以提供低碳發電方法,而後者可以符合道德標準。
未受社會現實的影響 - 過度誇大的說法 關於核電的商業可行性和 不道德的做法 在廢物處理方面 - 這裡有技術專家。
一些工程和經濟假設被認為是建立公眾討論基礎的堅實基礎,而不是有關核行為者歷史表現的公眾疑慮。
但有時我們希望能夠聽取更多專家的意見。 在28 9月南澳大利亞風暴過後,2016導致全州大停電,保守派議員 歸咎於風力發電 因為停電而且似乎在當場製定能源政策。
停電据說是一個 敲響了警鐘 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可再生能源對能源安全是一個不可靠的詛咒。
我們現在知道那些保守的議員了 被告知 澳大利亞電力市場運營商(AEMO)認為問題不是風力發電。
儘管 許多專家消除了風力發電等於停電的神話,複雜性 最終的AEMO報告 被捲入了 歪曲技術細節 在政治背景下 推諉.
澳大利亞的能源政策 顯然缺乏專家常識。
我們在這些故事中擁有的並不是什麼新鮮事。 柏拉圖建議我們把複雜的東西留給專家,亞里士多德建議我們把它留給人們。
這種緊張關係是否已經進行了爭論 知識專業 是共同利益或壟斷力量的來源。 我們大多數人直觀地掌握了這一點 專家可能是危險的,因為同樣的自治條件限制了他們的效用.
專家的僕人角色
如果專家可能是危險的,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限制他們在民主中的作用,而這些理由都不會讓人擔心科學不能絕對肯定地“了解現實”。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威脅 政治的“科學化”。 過多的專家意見可以縮小民主討論的範圍,因為科學分析和技術規劃在製定議程和確定社會選擇方面具有突出地位。
通過這種模式,我們的政治決策機製成為了現實 僅僅是科學知識分子的代理人.
第二個原因是 專家可能危及民主文明 因為信息不對稱。 專家可以說服其他專家和非專家。 但是,非專家努力說服專家,讓普通公民容易成為科學化政治遊戲中的輸家。
第三個原因是專家不成比例地定義了出於政治目的而被視為現實的東西。 例子包括危害的性質,機器的能力,以及關於技術問題的相關共識,政治討論可以根據這些技術問題制定。 這種專家對“真實”的影響是一種 民主國家的權力來源,所有權力都應該追究責任。
基於這些原因,您可以得出結論認為專家應該被視為 代表。 這是因為有人需要觀察觀察者,專家似乎就像一個需要的失敗機構 從自己身上拯救 通過對民主決定的目標負責。
民粹主義的下降
不幸的是,從那裡到一個更激進和民粹主義的位置只是一個短暫的跳躍。
激進主義依賴於專家和公民所代表的暗示 從技術到社會文化推理的兩極。 專家被描繪為僅限於抽象和非人格化的推理。
相比之下,普通公民被描繪為能夠進行更多共同敏感的推理 - 這種推理能更好地應對不確定性,意外和價值判斷。
因此,專家被視為一種易於感染他們所進入的任何交流交流的階級 獨斷論 讓專家像身體疾病一樣政治化。
這種激進的專家僕人角色版本迅速轉變為民粹主義。 如果民主是關於人民主權和多數人統治,自由民主的“自由主義”部分包括對獨立機構(如司法和新聞自由)的額外規定和對權利的保護(無論是民事,經濟還是文化),那麼民粹主義可以被認為是對自由民主多元化的挑戰。
民粹主義 是反精英主義,反多元主義,並呼籲人民的一般意志。 它也是一個 以薄為中心的意識形態 將自己插入更具體的政策提案中。
反多元主義在這裡指的是對民主內獨立機構合法性的強烈挑戰。 民粹主義者對權力偏離人民持謹慎態度。 所以,他們建議a 水密劃分 在權力結構和人民之間,據說可以保護人民免受那些沒有代表性和失去聯繫的機構的影響。
如果你想像專家在民主國家中集體組成一個結構鬆散,獨立的機構,那麼嚴格的僕人角色就會建議我們將專業知識作為一個機構與民主作為公民審議的論壇之間的分離。 因此,僕人角色支持民粹主義的反多元主義。
我們可以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這一點。 民粹主義者和專家的僕人觀念傾向於減少民主行動以開放問題。
當然,根據這些概念,邊緣化的處理方式也存在差異。 那些主張專家的僕人角色的人確實指出,權力不對稱會導致人員和問題的邊緣化。
有些人明智地指出, 既得利益和受限制的想像力 可以採取行動,以解決應該揭示其複雜性並為更廣泛的民主審查開闢的問題。
但民主還有另一面,它以審慎的方式結束了問題。 澳大利亞最近關閉了關於同性伴侶是否可以合法結婚,逐步投票的辯論“是“。 所有關於“開放”的民主言論都掩蓋了關閉某些事物的民主價值。
對於每個石棉的情況 專家低估了風險,我們可以找到像雷切爾卡森那樣的案例 “寂靜的春天” 專家揭示了風險。
每一個 臭氧洞 我們可以找到專家錯過公共損害風險的案例 煙草案件 專家們揭示了沒有政治利益的風險。
每一個 核案件 我們可以找到專家在民主審議和扼殺公民投入方面的錯誤 氣候變化案例 專家們已經很好地解釋了我們應該採取行動的原因,但公民卻因政治權宜的阻撓而陷入過濾。
專家的合作夥伴角色
因此,專家的僕人角色的概念有可能轉變為民粹主義 - 如果專家被視為傳染性的階級,和/或民粹主義者的反多元主義被隱含地複制,如果民主的減少只是“開放”也會隨之而來為了騎。
如果我們要將專家視為民主的合作夥伴,我們當然必須避免轉向技術專家。 這可以通過堅持僕人模型的注意事項來實現。
必須始終牢記政治科學化的風險,以及隱藏在專家與公民之間信息不對稱中的不可能性。
但專家的合作夥伴角色與專家的僕人角色有四種不同的關鍵。
其中一個是專家的合作夥伴角色明確抵制了專家是一個教條階級的暗示,類似於政治機構的交流和審議能力的疾病。 不能抵制這種暗示是民粹主義的道路。
第二,作為合作夥伴的專家讓我們思考專業知識在民主中發揮的積極作用。 有些人 政治理論家 和 社會科學分析家 有人認為,專業知識在多元化,複雜的世界中具有工具性。 它通過審議並賦予集體意志一旦它在某種政治上可操作的程度上合併。
專業知識作為一種消極的力量也是有用的,能夠作為國家,企業或公民(多數主義)企圖採取強制行動或被動不作為的反補貼機構。 在每種情況下,專業知識都被認為是機構在自由民主國家中發揮的各種職能作用的一個特例。
三,夥伴關於專業知識的概念明確否認權威關係權衡公民自治。 僕人關於專業知識作用的概念,尤其是當它們變得激進化並陷入民粹主義政治的反多元主義時,就很難放棄權衡假設。 豁免公民變得與邊緣化專家密切相關。
相比之下,合作夥伴的專業角色採用了不同的角色 權威關係模型。 隨著時間的推移,專家們對他們所遭受的爭論和批評 - 以及在不斷審查和挑戰的可能性的整體制度背景下是合理的。
公民在競爭和批評他們的信息和建議時並不會使專家邊緣化,只有專家在要求他們在潛在的審查和挑戰的背景下接受信息或建議時才會使公民邊緣化。 兩者都在多元化的自由民主制度中相互利用。
第四,儘管專家的僕人角色非常擔心權力關係可能影響公民自治的方式(因此希望專家和公民之間存在某種不透水的區分),但合作夥伴模式採取了自滿的態度。
民主專家的合作夥伴角色容忍跨職能領域的一些“洩漏”。 這種洩漏是雙向的,專家影響公民和公民影響專家,為女僕角色努力做的事情留出了相互說服的空間。
![]() 因此,民主專家的合作夥伴角色是構成Goldilocks“足夠”專業知識原則基礎的唯一可行候選人。
因此,民主專家的合作夥伴角色是構成Goldilocks“足夠”專業知識原則基礎的唯一可行候選人。
關於作者
Darrin Durant,科學與技術研究講師, 墨爾本大學
相關書籍
at InnerSelf 市場和亞馬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