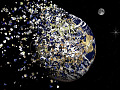當一群極端民族主義者在1919聚集在米蘭時,聽取了火炬手的領導 墨索里尼 他們說,他們成了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時刻的一部分。 在那裡,墨索里尼提出了一個不太可能的激進政治啟動的創始宣言。 它的名字是 Fascio di Combattimento兩年後作為運動名稱被採納的法西斯主義的卑微前兆。
從聚會開始的一個世紀,在政治荒野幾十年之後,“法西斯主義”又重新出現在新聞中 - 不僅是歷史記憶,而且是當代日益增長的威脅。 自從唐納德特朗普在2016美國總統選舉中取得轟動性的勝利以來,“法西斯主義何時回歸?”的問題已多次提出。 對民粹主義者的每次勝利來說,它也越來越響亮 睚Bolsonaro 在巴西或 利瑪竇Salvini 在意大利。
這個問題是可以理解和合法的。 這也很大程度上是誤導性的。 目前日常生活中的不禮貌爆發和對國際自由主義原則的敵意可能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是法西斯主義2.0,也不是我們應該擔心的主要問題。
喊得最響
民粹主義者似乎正在贏得通信游戲,大聲呼喊並且不斷推廣 分裂的消息。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在民意調查中獲得越來越多的選票。 與此同時,少數民族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口頭攻擊,有 如果當代民粹主義說話並表現得像“法西斯主義”,那麼很可能是法西斯主義。
但如果把焦點主要放在特朗普或其他當前反自由派反對派的名人身上,焦點就轉移到了“他們”,並且方便地將注意力從問題的核心轉移 - 在水底采捕業協會(UHA)的領導下, 自己的社會和信仰。 我們將挑戰視為來自某種與我們無關和陌生的極端主義。 這是為了痴迷於結果而不是原因。
事實上,目前民粹主義和不自由主義的崛起只是“從內部”的憤怒反彈。 這些運動是對主流自由主義政治的傲慢和缺陷的反應。 他們暴露了其壓裂的普遍合法性及其越來越無法解決不滿的深層原因。
如果一個人希望交換歷史類比,那麼人們應該記得,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沒有“法西斯主義者”在大眾的讚譽下獲得了權力。 他們只是被它推動了 民主制度的弱點 以及自由派精英本身的連續錯誤和錯誤估計。 過度強調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主義在1930s中摧毀中歐和南歐自由主義體系的成功可能是誘人的。 但同樣令人欣慰的是,將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僅僅視為對自由主義解體的威脅而非其症狀。
最後,如果特朗普或者說,這並不重要 Hugary的Viktor Orban 是“法西斯”還是別的什麼。 重要的是,他們是否能夠有效地操縱現有的 - 非常現實的 - 自由政治制度的功能失調以及主流社會對少數民族和非本土群體的毒性不規範化的焦慮。 重要的是,他們是否可以利用這些弱點來關閉思想和邊界,重振狹隘的社區視野,排除,沉默和迫害那些任意認為是陌生和威脅的人。
挑戰自滿
歷史上的似曾相識可能實際上在其他地方 - 不是所謂的極端分子或民粹主義者,而是在主流內部。 就像1930一樣,自由派精英可能高估了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力量和社會接受程度。 他們可能對無處不在的公民自我克制,對他人的同情和相互依賴感到自滿。 法西斯主義與否,當前的非自由民粹主義者及其不斷增長的支持者的品牌都來自主流社會中仍然存在的深層矛盾以及自由派精英的傲慢自滿。 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也打破了一個接一個的禁忌,並在不久的將來開闢了一系列以前無法想像或難以置信的激進行動的可能性。
在他作為仍然邊緣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領導人的早期演講中,阿道夫希特勒反思了他的政黨的作用和他的領導。 他說,它的目標是“提供劍”,然後更多的人可以更加猛烈地對抗他們的敵人。 現在世界再次充滿了能夠拿走那把劍的魅力人士。 他們哀嘆所謂的文明衰落,並宣揚民族復興和偉大的另類未來。 他們向一個看似龐大的皈依者講道,絕大多數人都不是極端分子,而是居住在主流社會。 他們正在煽動舊的恐懼,根深蒂固的偏見和新的焦慮 “入侵” 和身份稀釋。 他們還為其他人提供了工具和觀眾,使他們能夠走得那麼激進,積極進取的道路。
無論他們是什麼,這些人都面臨著我們政治制度的失敗以及我們主流社會中經常被忽視或噴塗的眾多矛盾。 必須停止它們 - 但只能通過解決導致其信息吸引其他許多其他因素的更深層次的社會原因:不斷增長的政治不信任,對快速變化的怨恨,日常生活中的困難。
當代民粹主義者的成功應該提醒大家,法新社可能已經在新西蘭人民解放陣線中被粉碎,因為戰後社會從此經常被告知; 然而,首先維持它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力量從未消失。 這可能是歷史上最有用的“教訓” - 沒有最終的勝利 - 或失敗。![]()
相關書籍
at InnerSelf 市場和亞馬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