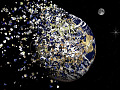根據具體情況,民粹主義是毒藥還是民主治療方法,或兩者兼而有之? Louis Boilly / Wikipedia Commons
如果不提及民粹主義的興起,就不可能關注新聞。 民粹主義曾經是一個很少使用的術語,在其他無關聯的政治背景下表示少數政黨,現在似乎幾乎是政治時刻的權威。
它還引起了專家的廣泛響應。 最常見的反應是對似乎出現的力量的負面反彈 威脅 民主。 極左翼和極右翼政治力量的出現似乎讓1930更加黯然失色,看看離開我們的地方。
另一方面,有一些有影響力的人物認為在民粹主義中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 遠非如此:民粹主義代表了一種吸引力 人民,並在此基礎上,不僅與民主一致,而且與任何尋求普遍吸引力的政治有關。
由於政黨尋求權力,廣泛的,如果不是普遍的,上訴就是他們所渴望的。 在這個問題上的民粹主義只不過是“政治的邏輯”,假設政治是公共或集體關注的問題。 非民粹主義政治注定會失敗,或者成為集體或身份的保護者 演示.
因此,民粹主義可以被定義為對民主具有威脅性和威脅性的東西,也可以被定義為對民主進行救贖,慶祝和表達的東西。 問題是,這兩種感官中的哪一種是正確的? 哪個更接近民粹主義的“真相”?
民粹主義作為民主的藥劑師
在著名的關於柏拉圖的Phaedus的文章中,雅克·德里達探索了“藥(pharmakon)“作為一個明顯具有自相矛盾含義的術語的例子。
Pharmakon,我們從中得出藥理學和藥學術語,表示一種有毒物質,用於使某人變得更好,但也可能殺死它們。
從這個意義上講,Pharmakon既有毒又有治愈作用。 它不可能是一個或另一個; 這兩者都是。 它是一種還是另一種取決於劑量,背景,身體對毒素的接受性等。 簡而言之,pharmakon表達生命和死亡的偶然性和可能性。
現在回想一下我們剛剛討論的與民粹主義有關的問題。 難道我們真的想說民粹主義總是和所有地方都是對民主的威脅,這是一種反對或恐懼的東西嗎? 在拯救民主方面,對於人民與腐敗或腐朽精英的訴求是否真的有意義 - 從它自身來看,是不是沒有時間或背景?
相比之下,我們是否真的相信,對人民的吸引力是政治的必要和建設性特徵,實際上是我們無法避免的事情? 難道我們不想說,是否要慶祝這種對人民與精英的吸引力取決於個體觀察者或參與者在政治選擇的漩渦中的地位?
民粹主義話語的出現 西班牙 伴隨著對政治精英的信心幾乎徹底崩潰。 數百萬人湧入2011的街道,抗議那些從總統府的奢侈品中榨取緊縮的人。
這是在腐敗,庇護主義和任人唯親的充分記錄的例子中的一個策略 - 更不用說公共資金在無用的大型項目上的非凡浪費,似乎在他們自己無能為力的污垢中揉搓普通人的鼻子。
所以民粹主義者的出現 我們可以 它的強烈信息是“是的,我們[人民]可以”。 然而,對於其他人來說,這聽起來是一種虛假的注意:害怕“魅力”,以領導者為中心的政治,以及扼殺並使街頭抗議者和微觀倡議無關緊要,從而在第一次創造條件地點。
民粹主義“從下面”的慶祝與對此的期待相混合 問題 即將到來 - 尤其是在勝利,媒體政治的大肆宣傳中切斷“下面”本身。
也考慮一下法國的出現 伊曼紐爾·馬孔,歐洲項目的中間派救世主。 通過巧妙的語義,他以一種巧妙的民粹主義策略反擊了民粹主義的勒龐的指控。
勒龐是生活在她批評的製度之外的“寄生蟲”,而不是他。 他是放棄精英的政治局外人; 她是精英的產物 - 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
與失敗的政治秩序聯繫起來,馬克龍沒有受到影響,而勒龐則因為陳舊的戰鬥和失落的法國而聞名。 他體現了法國的未來,她的黑暗和陰沉的過去。 不是戰鬥的royale,而是藥劑師的巴塔耶共和黨人。
但並非所有關於外人和精英的言論都不是因為有人賺了數百萬作為銀行家 羅斯柴爾德? 這個局外人的言論多久了 碰撞 預算削減和勞動力市場改革的現實?
將它的工作?
接受民粹主義和藥物的矛盾心理,那麼呢? 為什麼我們在這個術語上放了什麼樣的旋轉呢?
當代政治基本上成為一種重建民主的政治 崩潰 我們至少生活了兩個世紀的代表性敘事。 我們不太傾向於相信我們的代表和政治家的良好意圖。
我們已經成為民粹主義者,意識到精英們與人民脫節或脫鉤,因此我們自己。
我們似乎傾向於相信那些把自己定位為人民對抗精英的捍衛者的人,無論這種姿態多麼荒謬,並且幾乎沒有比億萬富翁房地產開發商更加荒謬的姿態讓自己成為人民的捍衛者反對精英。
我們不太確定“治療”會帶來什麼:選舉局外人(唐納德·特朗普, 傑里米·科比(Jeremy Corbyn), 威爾德斯)或假設某些非代表性或後代表性戰略將減少(如果不是消除)人民與政治權力之間的距離(審議大會, wikidemocracy, 流動民主).
我們不確定治愈,這個旺盛的局外人是否會“工作”並讓生活更美好,讓美國變得“偉大”,或者它是否會殺死政治石頭。
我們不確定代議制民主之後是否有生命,或者某種替代模式是否會更好或更失敗,讓我們的世界陷入癱瘓。 但是,我們傾向於進行實驗,因為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維持我們政治的確定性枯萎了。
![]() 我們看到毒素在希望和恐懼的混合下降 - 民粹主義:民主的藥物。
我們看到毒素在希望和恐懼的混合下降 - 民粹主義:民主的藥物。
關於作者
Simon Tormey,政治理論教授,社會與政治科學學院院長, 悉尼大學
本作者的書籍
at InnerSelf 市場和亞馬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