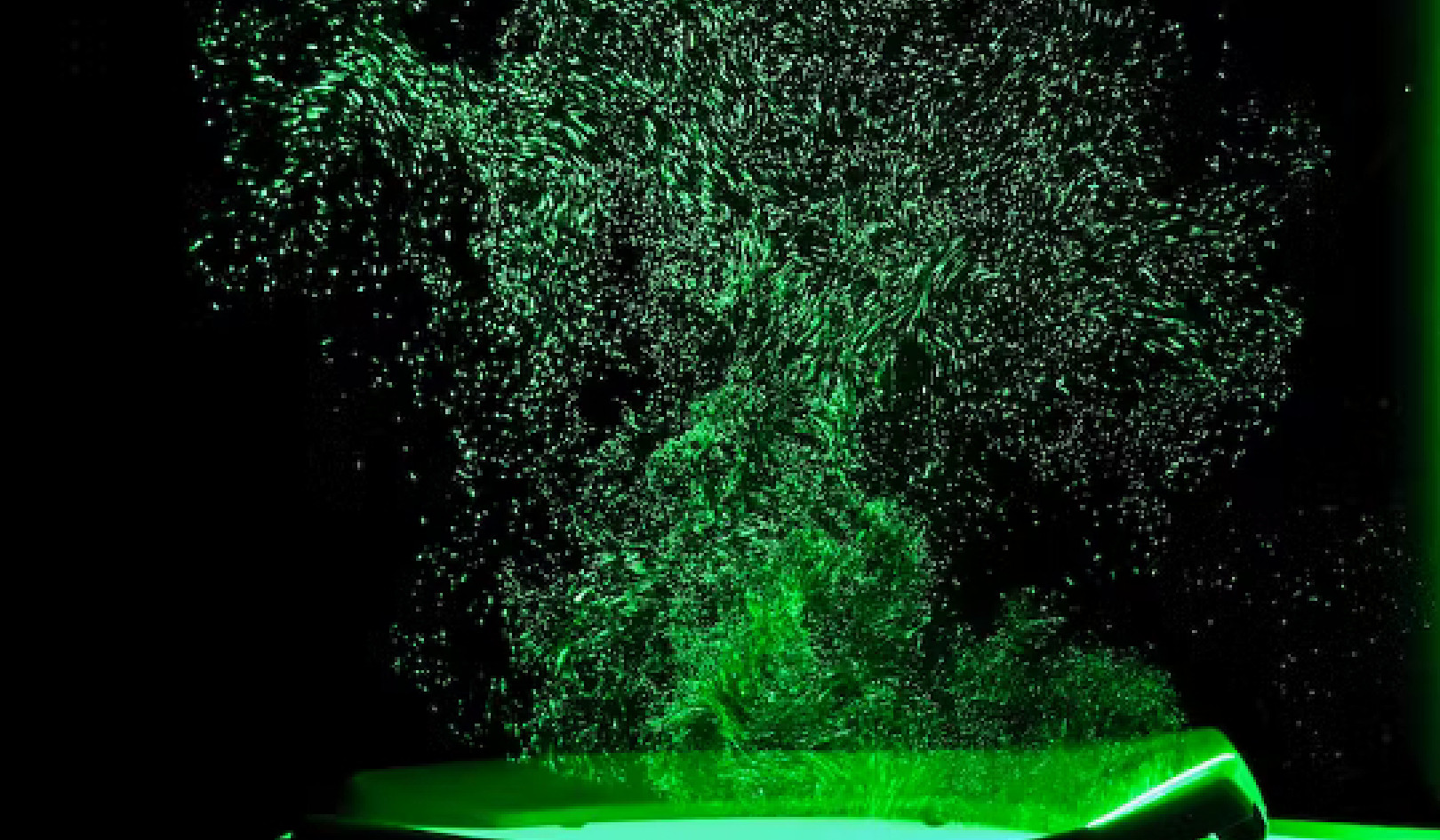讀詩。 攝影:Priscilla Du Preez/Unsplash,CC BY-SA
讀詩。 攝影:Priscilla Du Preez/Unsplash,CC BY-SA
近兩年來,美國人每天都面臨著不祥的消息。 我們生活在緊張的時期。 閱讀新聞感覺很糟糕; 無視它也感覺不對。
心理學家特麗·阿普特 最近寫了關於 “人類行為中的現像有時被描述為‘蜂巢轉換’,其中‘災難性事件消除了自私、衝突和競爭,使人類像超群居的蜜蜂一樣合作。”
但如果颶風、地震或火山觸發了蜂巢轉換,這個原理是否也適用於人為災難呢?
那些將孩子與父母分開的移民政策又如何呢? 校園槍擊、自殺、生態災難?
每天都有大量針對我們的令人恐懼和憤怒的新聞又如何呢?
面對這一切,人們幾乎不會蜂擁而至,形成合作蜂巢。 相反,我們的想像力、警覺性和同情心等人類品質似乎正在與我們作對。 想像我們同胞的痛苦和我們這個陷入困境的星球的未來會激起憤怒、恐懼和壓倒性的無助感。
如果有的話,我們能做什麼?
 塞內卡有答案。 讓·波爾·格蘭蒙, CC BY
塞內卡有答案。 讓·波爾·格蘭蒙, CC BY
聽塞內卡和愛比克泰德的話
憤怒和恐懼可能會演變成政治激進主義,但很難不覺得任何改變都太少、太晚了。
例如,與父母分離的孩子,即使他們都團聚了(這似乎不太可能),他們的餘生都會承受精神創傷,正如醫生丹妮爾·奧弗里(Danielle Ofri)所言。 在 Slate 中雄辯地指出.
人們應該如何反應 自殺率上升? 也許,從最近的報導來看,我們最希望做的就是聚集足夠的洞察力和事後諸葛亮,試圖阻止下一場災難的發生。
然而,今年春天的詳盡報導 一對名人自殺 – 安東尼·波登 (Anthony Bourdain) 和凱特·斯佩德 (Kate Spade) – 讓我回到 斯多葛派哲學家,在一世紀和二世紀蓬勃發展的思想家,特別是在羅馬。 這些哲學家對深奧的思辨不感興趣,他們強調倫理和美德。 他們關心如何生活和如何死亡。 斯多葛派心理學提供了並且仍然提供了與心靈合作的幫助,以平息我們的焦慮並幫助我們履行作為人類的職能。
布爾登和斯佩德都是富有創造力和成功的人物,是魅力和成就的象徵——尤其是布爾登,他對世界各個角落的不懈而勇敢的探索激勵了無數觀眾和讀者——事實證明他們都是弱勢群體。
威廉·B·歐文 (William B. Irvine),其 2009 年 《美好生活指南:堅忍快樂的古代藝術》“我一直在重讀,從他最喜歡的四位斯多葛派作家那裡得到了有用的提煉, 塞內卡, 愛比克泰德, Musonius Rufus 和 Marcus Aurelius,兩種對抗黑暗思想的斯多葛派顯著技巧。 我將通過提煉歐文來延續這一教學傳統。
塞內卡和愛比克泰德等作家的建議感覺非常切合實際。 經常提到的與自殺衝動相關的痛苦,例如恐懼和焦慮,是人類狀況的長期組成部分。 當我們談到一個有自殺傾向的人與惡魔搏鬥時 – 一個與荷馬一樣古老的詞 – 這就是我們正在討論的。
斯多葛學派教導說,你可以嘗試對抗你的惡魔——不是通過談話療法,更不用說藥物,而是通過與你的思想合作。
準備好
第一種技巧是消極想像:想像最壞的情況,以便做好準備。
最壞的情況很可能永遠不會發生。 可能發生或可能發生的壞事可能比你能想到的最糟糕的事情要溫和。 你會因為最壞的情況還沒有發生而感到欣慰,同時也會在精神上對最壞的可能性有所支持。
“他剝奪了當前弊病的力量,” 塞內卡寫道,“誰能提前察覺到他們的到來。”
在其他地方, 塞內卡寫道,“生長在陽光充足的山谷中的樹木很脆弱。 因此,它對好人有利,使他們能夠無憂無慮地生活,與危險保持親密關係,並平靜地承受命運,而命運只對那些承受不幸的人來說是不幸的。”
偽裝成瘋狂湯姆的埃德加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觀點,他在《李爾王》中觀察到: “最糟糕的還不是/只要我們能說‘這是最糟糕的。’” 能夠對事情有多糟糕發表評論——這種哀嘆現在已經成為我們許多人的日常儀式——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我們活了下來。
分而治之——或不分而治之
歐文稱之為第二種斯多葛式的自助技巧 控制的二分法:將情況分為您可以控制的情況和您無法控制的情況。
愛比克泰德 觀察到 “在存在的事物中,宙斯將一些置於我們的控制之下,而另一些則置於我們的控制之下。 因此……我們必須把自己能掌控的事情絕對放在心上,而不能掌控的事情則交給宇宙。”
 愛比克泰德也有一些答案。 波士頓公共圖書館的約翰·亞當斯圖書館
愛比克泰德也有一些答案。 波士頓公共圖書館的約翰·亞當斯圖書館
歐文 添加第三類,從而將二分法轉變為他所說的三分法:我們無法控制的事情、我們完全控制的事情以及我們有一定程度控制的事情。
我們無法控制明天太陽是否升起。
我們可以控制是否要第三碗冰淇淋、選擇穿什麼毛衣或是否按“發送”。
至於自殺、校園槍擊、與父母分離的痛苦孩子? 我們可以做點什麼。 我們可以投票、競選公職、組織、捐獻金錢或物品。 在這些事業中,我們可以與鄰居和同事合作,盡可能像蜂巢一樣行動,而不會因痛苦而癱瘓。
打棒球、去公園
那些有幸體驗過私人歡樂的人仍然感受到公眾恐懼的陰影。 然而喜樂仍是喜樂; 生活還是需要過的。
如果我們是棒球運動員,我們就可以打棒球。 如果我們是祖父母,我們可以帶孫子去公園。 我們不僅可以閱讀新聞,還可以閱讀小說和歷史,讓我們擺脫當下的束縛。 我們可以閱讀詩歌,它有能力提煉我們的時代,使我們的道德困境即使不能完全解決,也能清晰地表達出來。
如果我們是詩人,我們就可以寫詩——通常這不是一個社區的事業,但現在什麼是普通的呢? 公共痛苦滲透到私人生活中,一些最好的新詩將公共和私人結合在一起。 我自己既讀詩又寫詩——這兩項活動我都可以很好地控制。 我讀過的詩很引人入勝。
最近一首雄辯的詩涵蓋了家庭與無家可歸、安全與危險之間的道德不和諧, AE 斯託林斯的《同理心》“
有趣的是,斯多葛派的消極想像概念激發了這首詩的論點:我和我的家人舒適地躺在家裡的床上,而不是在黑暗中在木筏上翻來覆去,這真是太好了。 情況可能會更糟:
我的愛人,今晚我很感激
我們的房源床不是木筏
岌岌可危
當我們躲避海岸警衛隊的燈光時……
在這首詩的最後一節中,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同理心這個簡單的概念,認為它是自以為是、膚淺和虛偽的:
同情心並不慷慨,
這是自私的。 這可不太好
說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不要成為那些願意為我們而死的人。
拒絕什麼詩人 威廉·布萊克 (William Blake) 稱“單一願景”,斯託林斯勇敢地看到了雙方,並且似乎奇蹟般地從雙方的角度進行了寫作。
她還設法在兩邊生活。 在過去的一年半里,她一直在與 雅典的難民婦女和兒童.
 詩人 AE Stallings 與雅典的難民兒童一起創作手韻和歌曲。 照片:麗貝卡·J·斯威特曼, 作者提供
詩人 AE Stallings 與雅典的難民兒童一起創作手韻和歌曲。 照片:麗貝卡·J·斯威特曼, 作者提供
我們這個時代翻騰的黑暗暗流也可以在 安娜·埃文斯的《不是我的兒子》 維拉內爾的韻律包括“邊界”、“秩序”、“混亂”、“無視她”、“懇求她”和“走向她”,伴隨著不祥的音樂。
像《同理心》和《不是我的兒子》這樣的詩讀起來並不舒服,想必寫起來也不是很舒服。 但它們代表了我們這些碰巧成為詩人的人所能做的事情的衡量標準。 我寧願接受這些詩人深思熟慮、雄辯地呈現的可怕消息,也不願直接閱讀頭條新聞。
我的下一個系列將被稱為“愛與恐懼”。 斯多葛學派知道恐懼始終是畫面的一部分。![]()
關於作者
相關書籍
at InnerSelf 市場和亞馬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