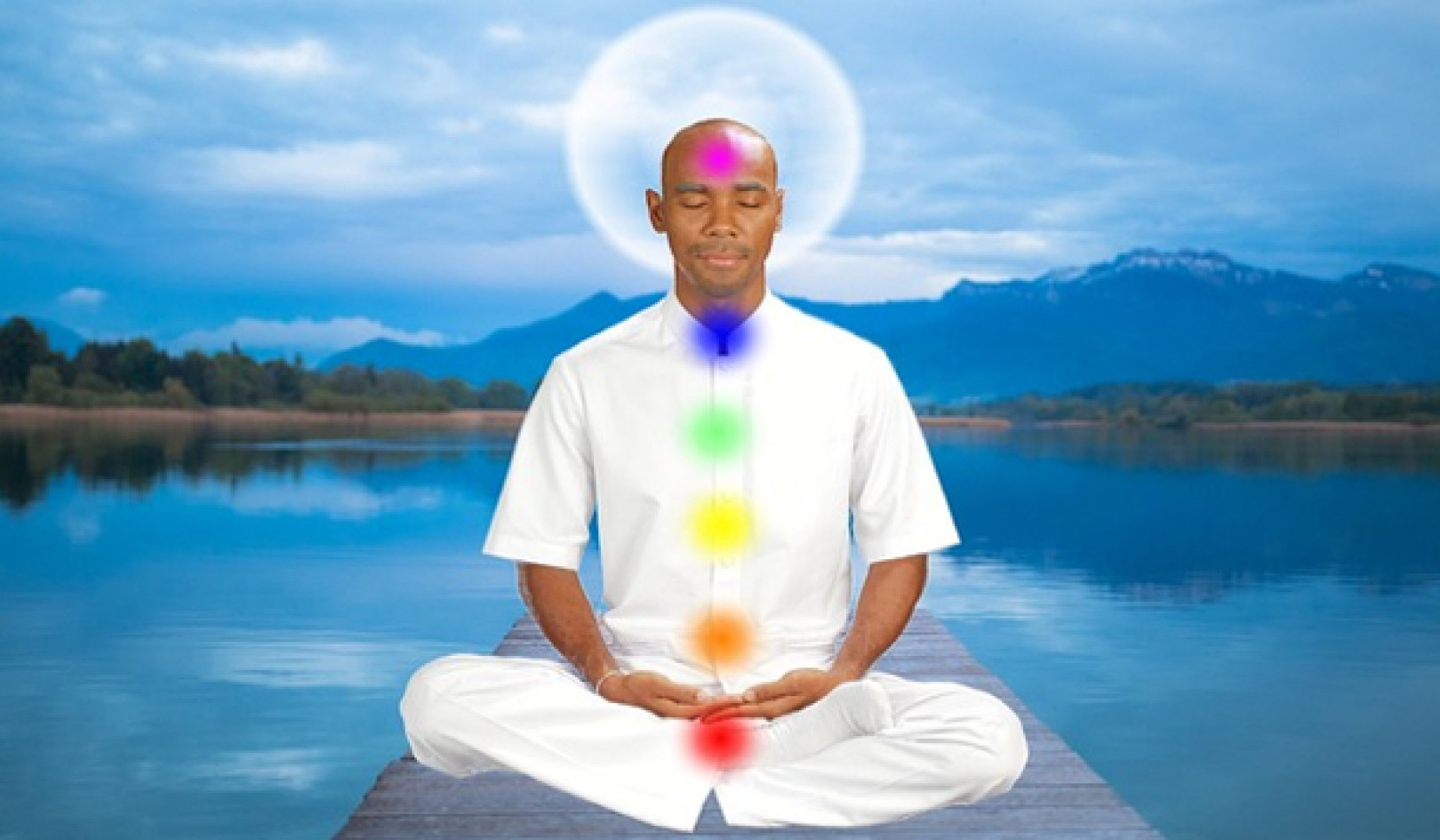約翰奧蘭多帕里,'倫敦街景',1835。 ©Alfred Dunhill Collection(維基共享資源)
約翰奧蘭多帕里,'倫敦街景',1835。 ©Alfred Dunhill Collection(維基共享資源)
在信息時代,我們經常被告知。 這是一個痴迷於空間,時間和速度的時代,社交媒體灌輸虛擬生活,與我們的“真實”生活平行,並且通信技術在全球範圍內崩潰。 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在努力轟炸我們收到的信息,並因新媒體而感到焦慮,我們認為這會威脅到我們的關係和人類互動的“通常”模式。
雖然技術可能會發生變化,但這些擔憂實際上已有很長的歷史:一個多世紀以前,我們的祖先也有同樣的擔憂。 文學,醫學和文化 回复 在維多利亞時代,人們認識到壓力和過度勞累的問題,這預示著我們自己時代的許多關注程度可能會令人驚訝。
英國諷刺周刊Punch的以下1906漫畫很好地說明了這種平行關係:
標題寫著:“這兩個數字沒有相互通信。 這位女士收到了一條愛情信息,而這位紳士正在接受一些比賽結果。“無線電報”的發展被描繪成一種壓倒性的隔離技術。
用智能手機取代這些奇怪的裝置,讓我們想起許多當代抱怨年輕人的社交和情感發育不良,他們不再親自出去,而是在虛擬環境中,往往身體距離很遠。 不同的技術,同樣的聲明。 而且,同樣的焦慮在於“真正的”人類互動越來越受到技術創新的威脅,我們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將其融入日常生活中。 通過使用這樣的設備,所以流行的偏執狂會有它,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自己。
聲音的雜音
19世紀見證了印刷業的迅速發展。 新技術和大眾出版格式引發了更為普遍的期刊新聞,獲得了比以往更廣泛的讀者群。 許多人慶祝即時新聞和更多溝通的可能性。 但人們對於那些不堪重負的中產階級讀者提出了擔憂,人們認為,這些讀者缺乏批判性判斷新信息量的辨別能力,因此以膚淺,不穩定的方式閱讀所有內容。
例如,哲學家和散文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對生活各個方面機械干預造成的社會和自然的新缺乏直接接觸感到遺憾。 印刷出版物正迅速成為公眾辯論和影響的主要媒介,他們正在塑造, 在卡萊爾看來,扭曲了人類的學習和溝通。
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衷心同意,表達了他的恐懼 在一篇文章中 題為“文明”。 他認為聲稱壓倒一般公眾的聲音的雜音正在創造:
一種社會狀態,任何聲音,而不是誇張的鑰匙,都在喧嘩中丟失。 在如此擁擠的領域取得成功不取決於一個人是什麼,而是取決於他看起來如何:僅僅是有市場品質成為對象而不是實質性對象,而一個人的資本和勞動力在做任何事情上花費的少於說服其他人做到了。 我們這個時代已經看到了這種邪惡的完美。
個人作家和作家正在變得無能為力,迷失在充滿思想,觀點,廣告和庸醫的市場中。
老抱怨
與我們自己社會關注的相似之處是驚人的。 與現代的獲取信息手段相比,並沒有提出任何不同線路的爭論,例如 Twitter, Facebook,我們不斷訪問 因特網 在一般。
在他的2008文章中,“谷歌讓我們變得愚蠢嗎?“記者尼古拉斯·卡爾(Nicolas Carr)推測,”在我們閱讀和思考的方式中,我們可能正處於一場大變革之中“。 在網上閱讀,他認為,不鼓勵在文本中長時間深思熟慮,傾向於通過超鏈接跳過,掃描和離題,這最終會削弱我們的注意力和沈思能力。
作家也分享了卡爾的焦慮。 菲利普·羅斯 和 自我例如,他們都預言這些趨勢會導緻小說的死亡,他們認為人們越來越不習慣並且沒有能力參與其特有的長線性形式。
當然,所有舊技術都曾經是新技術。 人們有一點真正關心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現在完全無害。 在19世紀後期的幾十年裡,人們認為電話會引起耳聾,而且硫磺蒸汽會使倫敦地鐵上的乘客窒息。 這些新的進步正在取代舊的靜止技術,這些技術本身也會引入類似的焦慮。 柏拉圖,隨著他的口頭文化開始向文學轉型,他嚴重擔心寫作本身會侵蝕記憶。
雖然我們不能對19世紀對電報,火車,電話和報紙等技術的態度與我們自己作為互聯網和手機出現的文化的反應進行過於嚴格的比較,但有一些相似之處。差點反對 勒德 位置。 隨著技術的變化,我們至少在我們看待它的方式上仍然出乎意料地保持不變。
關於作者
Melissa Dickson,牛津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相關書籍
at InnerSelf 市場和亞馬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