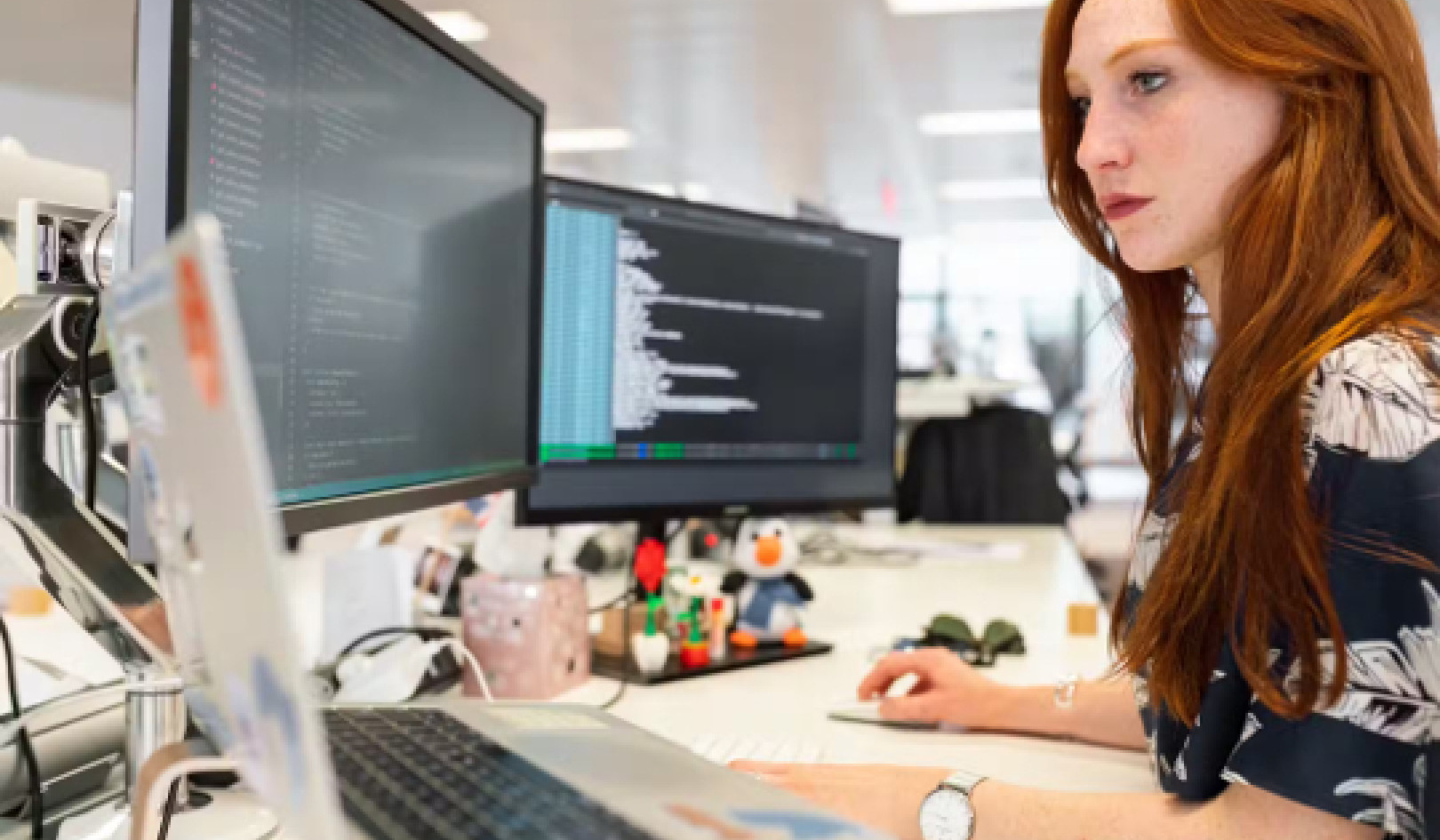希臘英雄阿基里斯(Achilles)身為特洛伊戰爭的主要對手赫克托(Hector)的屍體。 Jean-Joseph Taillasson /克蘭納特美術館
隨著三月份冠狀病毒大流行襲擊紐約,死亡人數迅速上升,家庭和社區幾乎沒有機會為親人表演傳統儀式。
記者 時代雜誌描述 如何將屍體放在坡道上,然後放在裝卸平台上並堆放在木架子上。 設立了緊急太平間來處理大量死者。 根據官方統計,僅紐約市就有 20,000死 在兩個月的時間內。
幾個月後,由於人們一直對冠狀病毒的威脅以及觀察到社會距離的恐懼,使我們哀悼和處理死亡的能力仍然受到破壞。
作為一個 古典學者,我傾向於回顧過去以幫助理解現在。 古代文學,特別是古希臘史詩,探索了成為人類和社區一部分的意義。
荷馬在希臘經典著作《 The Iliad》中幾乎沒有規定普遍權利,但顯而易見的是人們對適當的哀悼,埋葬和紀念的期望。
珍視死亡中的生命
荷馬的《伊利亞特》以長達約10天的敘述方式探討了50年戰爭(特洛伊木馬戰爭)的主題。 它顯示了希臘人為抵禦特洛伊人而進行的內部鬥爭和鬥爭。
它通過強調損失和苦難的規模,而不僅僅是國王和軍閥的誇張性質,使特洛伊市變得人性化。
史詩 從認識開始 它的主要角色阿喀琉斯之怒,由於對他的榮譽有些微的榮譽,“為希臘人製造了無數的悲傷”,並“向黑社會派遣了許多強大的英雄”。
史詩般的衝突 啟動 當希臘軍隊首領阿伽門農國王剝奪了半神的英雄阿基里斯·布里塞西斯(Briseis)時,他是一名被奴役的婦女,在戰爭初期曾被授予獎品。
據說布里塞斯(Briseis)是阿基里斯(Achilles)的“格拉斯(geras)”,這是表明他的希臘同胞對他的尊敬的物理標記。 “ geras”一詞的含義隨著詩歌的發展而發展。 但是,隨著讀者與阿喀琉斯人一起學習,無論如何,當一個人要死時,物理對象實際上是毫無意義的。
到史詩末期,重要的物理信物已由埋葬儀式代替。 宙斯(Zeus)接受他的凡人兒子撒皮頓(Sardedon)充其量只有在他 埋葬和哀悼。 阿基里斯(Achilles)也堅持認為,哀悼是希臘人聚集時的哀悼,是“死者的geras” 紀念他的同志Patroklos.
史詩結尾處有葬禮阿基里斯的對手赫克托(Hector)的理由,赫托克是特洛伊木馬戰士中最大的戰士,也是阿基里斯憤怒的另一位受害者。
對於赫克託的葬禮,希臘人和特洛伊人都同意停戰協定。 特洛伊人收集並清理赫克託的屍體,將他火化,並將其遺體埋在一個巨大的墓穴下。 這座城市的女性講述了勇敢英雄的故事 在他們的哀嘆中.
這是它的基本敘述-葬禮對於社區的集體工作至關重要。 不遵守葬禮會引發危機。 在伊利亞特,眾神見面解決 赫克托未埋身的問題:阿喀琉斯必須停止憤怒,將赫克託的遺體還給家人。
神的權利
在其他古希臘神話中也重複了這種敘述。 也許最著名的是Sophocles的“ Antigone”,這是一部公元前440年代的希臘悲劇。在該劇中,兩個兄弟Eteocles和Polynices在為控制這座城市而戰中被殺。
叔叔克里昂(Croon)接管了這座城市, 禁止埋葬一個。 戲劇的衝突集中在他們的姐姐安提戈涅(Antigone)身上。安提戈涅(Antigone)將哥哥埋葬於新國王的遺願中,使自己喪命。
在反對這項基本權利時,克里昂被證明依次遭受痛苦,在此過程中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和兒子以自殺。 為了對安蒂戈涅因執行其兄弟的儀式而判處死刑,他的兒子海蒙(Haemon)喪生,其母親尤里迪斯(Eurydice)跟隨他。
從這個角度來看,正確地紀念死者,特別是那些為人民服務而死的人,是一項神聖的權利。 此外,對死者的虐待給這座城市帶來了恥辱和污染。 瘟疫經常詛咒那些無法紀念他們墮落的城市和人民。
這是“供應商”,這是另一部希臘劇,向我們講述了希臘底比斯國王俄狄浦斯的兒子之間的衝突。 在Euripides的這齣戲中,Thebans拒絕埋葬任何與自己的城市作戰的戰士。 只有當雅典英雄These修斯領導一支軍隊強迫他們向死者致敬時,危機才能得到解決。
古典修辭學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將死者尊為公職。 希臘歷史學家Thucydides撰寫了Pericles的葬禮演說,Pericles在公元前430年代曾是雅典的著名領袖
在提供“附子”,佩里克利斯(Pericles)表達了他對雅典人過去抵禦外國威脅的立場的看法。
過去的回憶是通往未來的重要指南。 這就是為什麼葬禮在雅典的生活中變得如此重要的原因:它提供了一個機會,解釋為什麼為了共同的公民使命和身份而犧牲這些生命。
記憶社區
即使在今天,回憶還是被故事所塑造。 從當地社區到國家,我們講述的故事將塑造我們對過去的記憶。
美國衛生計量與評估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預測,在美國估計有200,000人死于冠狀病毒 到26月XNUMX日 到年底約有400,000萬。
許多看到親人死亡的人將面臨無法解決的損失,或者“複雜的悲傷”-悲傷是由於不知道親人發生了什麼或沒有社會結構來處理他們的損失而引起的。 That grief has been compounded by the current isolation.當前的隔離使這種悲傷更加複雜。 It has prevented many from carrying out those very rites that help us learn to live with our grief.它阻止了許多人執行那些幫助我們學會忍受痛苦的儀式。
就在最近,我失去了我91歲的祖母, 貝弗利·喬爾斯內斯,導致非冠狀病毒死亡。 My family made the hard decision not to travel across the country to bury her.我的家人做出了艱難的決定,決定不去全國各地埋葬她。 Instead, we gathered for a video memorial of a celebration of a life well-lived.取而代之的是,我們聚在一起觀看了一段慶祝過上美好生活的錄像帶。 As we did so, I could see my family struggling to know how to proceed without the rituals and the comfort of being together.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可以看到我的家人在不遵循儀式和舒適地在一起的情況下艱難地知道如何繼續前進。
不允許集體面對面紀念的悲痛可能變成 虛弱的創傷。 Our public discourse, however, when it has not tried to minimize the number of the dead or the continuing threat, has not sought to但是,我們的公共話語沒有試圖減少死者人數或持續威脅的數量,就沒有試圖 提供任何紀念計劃,現在或將來。
What Homer and Sophocles demonstrate is that the rites we give to the dead help us understand what it takes to go on living.荷馬和Sophocles證明的是,我們給死者的儀式有助於我們理解繼續生活所需要的東西。 I believe we need to start honoring those we have lost to this epidemic.我相信我們需要開始表彰那些在這一流行病中喪生的人。 It will not just bring comfort to the living, but remind us that we share a community in which our lives – and deaths – have meaning.它不僅會給生活帶來安慰,而且提醒我們,我們擁有一個共同的社區,在這個社區中,我們的生死攸關。![]()
關於作者
古典學副教授Joel Christensen, 布蘭代斯大學
books_de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