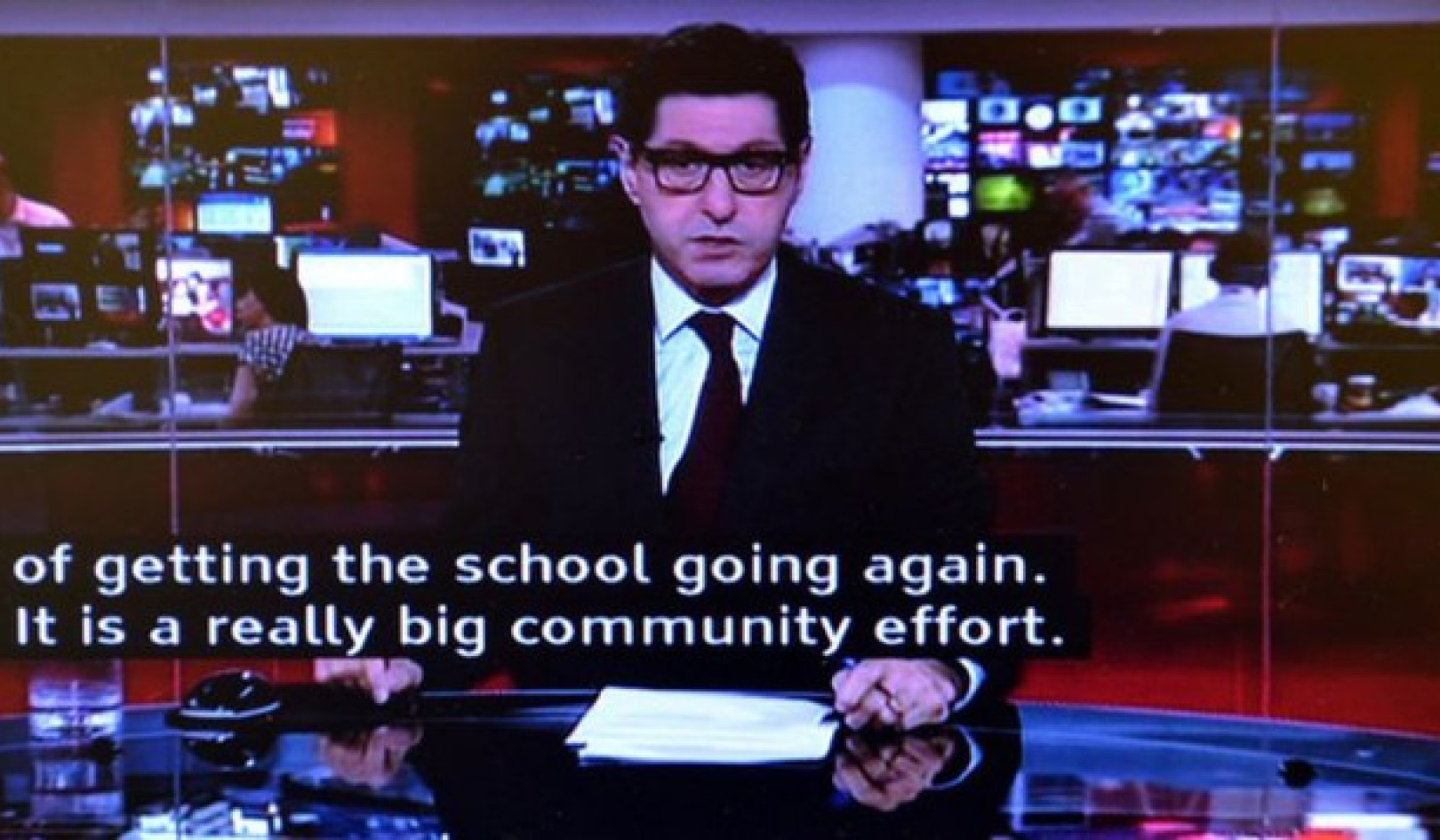你聽到那個音樂嗎? 太美了!
這是我聽過的最美好的事情。
再見。
- Claire,Final Words項目參與者,
在死前幾個小時給她長大的孩子
除了引用著名的聰明退出線的選集和網站之外,關於最終單詞的文章很少。 他們包括像喜劇演員鮑勃霍普和他的妻子那樣的談話記錄,她的丈夫迅速衰落而驚恐地告訴他:“鮑勃,我們從來沒有安排過你的葬禮。 親愛的,你想在哪裡埋葬? 我們必須弄清楚這一點。 你想在哪裡被埋葬?“
他的反應是典型的干澀機智:“給我一個驚喜!”
正如通常的情況一樣,希望是真實的性格。
蘋果史蒂夫喬布斯驚嘆不已 - “哦,哇! 哦,哇! 哦,哇!“ - 是我們在門檻上聽到的強化語言的一個例子,並且對於受到啟發的創新者的個性是真實的。
另一位著名的先驅托馬斯愛迪生在昏迷時出現昏迷,睜開眼睛,向上看,說:“那裡非常漂亮。”他的話代表了那些盯著他們的人。門檻。
名人評論家羅傑·埃伯特(Roger Ebert)的妻子查斯·埃伯特(Chaz Ebert)分享了她丈夫的遺言, 男性尊稱 2013在:
羅傑去世前一周,我會看到他,他會談到去過這個地方。 我以為他是幻覺。 我以為他們給了他太多藥。 但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給我寫了一張紙條:“這都是一個精心設計的惡作劇。”我問他,“什麼是惡作劇?”他正在談論這個世界,這個地方。 他說這完全是一種錯覺。 我以為他只是困惑。 但他並沒有感到困惑。 他沒有去天堂,不是我們想到天堂的方式。 他形容這是一個你甚至無法想像的浩瀚。 這是一個過去,現在和未來同時發生的地方。
這些引人注目的詞語被全國各地的人們所著迷所吸引 - 而且我所研究的那些人在床邊聽到了這些詞彙的真實複雜性。
然而,對於我們其他不是名人的人來說,我們的最後一句話是未經編輯的,未及時記錄下來的。 然而,我們所有人在臨終前都得到了一個平台。 每天都會說出令人信服的最後一句話 - 而且它們很少像我們在書籍和雜誌的封面之間那樣簡單或聰明。 許多最後的單詞不那麼直觀,不太容易理解,而且更加神秘 - 而且它們的複雜性使它們更加卓越。
生命盡頭的神聖語言
我們的最後一句話深刻反映了我們是誰,對我們最重要的是什麼。 即使是處於昏迷狀態的人和那些多年沒有溝通的人,也可能在他們死之前說話,提出建議,原諒,愛,甚至用朋友和家人留下神秘的短語,例如“不是那樣”,“代名詞全是錯的,“”我把錢留在第三個抽屜裡,“或者簡單的”謝謝你。 我愛你。”
佛教徒相信,反思我們的遺言可能會加深我們對生命無常的接受,並提醒我們品嚐當下的時刻。 在佛教徒和印度教的信仰體系中,垂死的人們提供分離的智慧話語一直是一種傳統。 一些和尚甚至在最後時刻創作了詩歌。
那些正在死去的人通常被認為可以獲得生活中無法獲得的真理和啟示。 最後的話被認為是對我們生活的金色印章,就像一張總結我們所有行為和日子的郵票,讓我們周圍的人知道我們相信什麼,真正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所有人總有一天會說出,想到或夢想我們的最後一句話。 有一天,我們大多數人都會在其他人的床邊。 對於我們這些生活中的人來說,超越門檻的存在是一個謎 - 就像所有來到我們面前的人一樣。
追踪最終詞語的路徑
許多有趣的問題仍然存在於生命末期的語言,認知和意識中。 從“最後的話語項目”的非正式研究來看,我們生活中的人是誰,我們在死亡中; 當我們的語言讓位於越來越具象和無意義的表達時,我們越過門檻,用我們生活敘事的符號,隱喻和意義進入另一個維度或觀察方式。
通過尊重生命終結的語言 - 包括我們無法理解的語言 - 我們可以更好地尊重我們在最後的日子裡所愛的人,並最終更好地理解與死亡相關的認知過程。 像我們一樣,我們將與他們建立更深層次的關係,留下更有意義的回憶,以及我們對來世問詢的可能答案。
寫下我們所愛的人的遺言可能會導致與該人的洞察力和和諧感。 通過對重要時刻的隱喻實例,臨終的人通常通過使用與生命相關的符號來談論即將到來的重要時刻或重要時刻,使我們知道死亡臨近。 我們還聽到與旅行或離開相關的隱喻,並且數據表明這些隱喻通常具有外部代理機構。 就是說,一般來說,垂死的人們在談論等待運輸工具-他們外面的東西將他們帶走。
Final Words項目的非正式研究,以及過去和現在數十年中進行的更為嚴格的研究表明,人們看到並與死者一起交流。 並且,當他們這樣做時,這些願景和探訪常常伴隨著深遠的和平,這通常與藥物相關的幻覺有所不同。
垂死之聲中出現的圖像通常與說話者的個性和生活故事相一致,並且這些圖像有時在持續的敘事中發展幾天甚至幾週。 我們可能會發現令人著迷且複雜的重複,例如“悲傷中如此之多”或“此寬度擴大了多少?” 我們可能會聽到自相矛盾的言論或混合語言,在其中看來,我們所愛的人站在兩個世界之間,例如有人要求戴眼鏡以更好地欣賞面前的風景時。 就像我們所愛的人似乎永遠消失在黑暗中一樣,我們可能會看到清晰度的飛躍。
這些是你在床邊或發現自己處於生命門檻時可能會發現的垂死語言的一些顯著特質。 你可能已經或可能有一天會見證突然的清醒。
我們可能會聽到提高意識或獨特意識的話,或者要求寬恕與和解的消息,或者我們可能有共同的死亡經歷,在這些經歷中,我們自己似乎擺脫了時間和地點的一般限制,似乎與我們的生活更加融洽了。心愛的人。 我們中的某些人可能具有與以往不同的不尋常的心靈感應或符號通信。 其他人可能會注意到親人告訴我們死亡即將來臨的許多方式,例如我父親宣布天使告訴他只剩三天了。
看來,當我們接近死亡時,大腦中與文字思維和語言相關的區域產生了一種新的說話和思維方式。 這種轉變可能代表著一個更大的運動,從這個維度轉向另一個維度,或者至少是另一種思維,感覺和存在方式。 當我們看待瀕臨死亡的話語時,我們會發現語言經常形成一個連續體,而這個連續體似乎與腦功能相關。 連續體跨越了文字,象徵性和難以理解的語言,最後是非語言甚至是心靈感應的交流。 文字是五種常識中的普通現實語言; 它是有目的性和可理解的語言。 腦部掃描顯示,字面語言例如“那把椅子上有四個棕色的腿和一個白色的墊子”與左半球接合。 左半球容納了傳統上被認為是語音中心的區域。
但是,當人們用隱喻說話時,結果是不同的。 諸如“那把椅子看起來像考拉熊的椅子”之類的句子同時涉及左右腦半球。 傳統上,右半球與生活中無法言喻的方面相關:音樂,視覺藝術和靈性。 隱喻似乎是兩個半球之間以及可能存在的兩種不同狀態之間的橋樑。
廢話的最新發現和早期發現表明,它可能與大腦中與目的性語言無關的部分有關,這可能與音樂和神秘狀態有著更緊密的聯繫。 說廢話可能更像是音樂,因為它非常依賴語言的節奏和聲音而不是其含義。 看來,我們生命後期大腦功能的明顯降低可能與無意義的語言以及超人和神秘狀態相關。
一種新的先驗意義
那麼,也許我們在生命的盡頭就渴望獲得超凡的經驗。 許多瀕死經歷的倖存者說,他們死後進入了一個沒有空間和時間的世界。 垂死的語言似乎也表明了方向的改變。 表示運動和旅行的短語(例如“幫助我從這裡下來”)來自躺在床上相對不動的人。 這種語言似乎表明人們在太空中對自己的看法發生了巨大變化。 因此,它們對介詞(那些描述位置的小詞)的使用也是如此。
當我們死去的時候,我們大多數人都會從文學現實的感性語言轉向更無意義的,非感性的,甚至是多感官的意識。 那些瀕臨死亡經歷的人的語言模式跟踪了非常相似的軌跡。
也許我們在生命末期看到的語言變化是發展新意識的過程的一部分 - 而不是廢話。
聽力正在癒合
當我們見證死亡的語言時,我們被邀請與我們的愛人一起進入新的領域。
當你坐在死亡旁邊,打開你的心臟。
並記住,聽力正在癒合。 當你仔細聆聽時,你可能會發現你的愛人為你提供了洞察力和保證 - 即使是在第一次聽到他們時可能令人費解的話。
我們對門檻的語言越是放鬆,我們就能給那些正在死去的人以及所有親愛的人帶來更大的安慰。
我問聖塔芭芭拉臨終關懷醫院的斯蒂芬·瓊斯(Stephen Jones),他是否願意分享一些與處於臨界點的人交流的智慧。 他寫信給我說:“垂死的人需要我們成為傑出的聽眾,才能被理解。 當通過我們的心g接受垂死的語言時,最好的理解是。 每個音節都是神聖的,應該作為禮物接受。”
©2017 by Lisa Smartt。 經許可使用
新世界圖書館,諾瓦托,CA。
www.newworldlibrary.com
文章來源
門檻上的話語:我們在接近死亡時所說的話
作者:Lisa Smartt。
 當她的父親患有癌症晚期時,作家麗莎·斯瑪特開始記錄他的談話,並注意到他的性格發生了莫名其妙的變化。史瑪特的父親曾經是個具有世俗世界觀的懷疑論者,但在他最後的日子裡形成了深刻的精神觀?他的語言發生了變化。出於困惑和好奇,史瑪特開始調查其他人在瀕臨死亡時所說的話,透過訪談和筆錄收集了一百多個案例研究。
當她的父親患有癌症晚期時,作家麗莎·斯瑪特開始記錄他的談話,並注意到他的性格發生了莫名其妙的變化。史瑪特的父親曾經是個具有世俗世界觀的懷疑論者,但在他最後的日子裡形成了深刻的精神觀?他的語言發生了變化。出於困惑和好奇,史瑪特開始調查其他人在瀕臨死亡時所說的話,透過訪談和筆錄收集了一百多個案例研究。
點擊此處獲取更多信息和/或訂購此平裝書 和/或下載 Kindle版。
關於作者
 Lisa Smartt,MA,是語言學家,教育家和詩人。 她是“門檻上的話語:我們即將死亡時所說的話”(新世界圖書館2017)的作者。 這本書是基於通過收集的數據 最後的話語項目,一項正在進行的研究,致力於收集和解釋生命末期的神秘語言。 她與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密切合作,以他對語言的研究為指導,尤其是難以理解的語言。 他們在大學,臨終關懷和會議上共同推動了有關語言和意識的演講。
Lisa Smartt,MA,是語言學家,教育家和詩人。 她是“門檻上的話語:我們即將死亡時所說的話”(新世界圖書館2017)的作者。 這本書是基於通過收集的數據 最後的話語項目,一項正在進行的研究,致力於收集和解釋生命末期的神秘語言。 她與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密切合作,以他對語言的研究為指導,尤其是難以理解的語言。 他們在大學,臨終關懷和會議上共同推動了有關語言和意識的演講。
相關書籍
at InnerSelf 市場和亞馬遜